夜郎文学年第56期荐读袁
在清晨的月台前,仔细地看,屏住呼吸,将思绪扭成一股上升的细绳,晨曦中的石砖路面便摇晃起来,石子和斑点忽大忽小,开始旋转,流动着,胶着地,凝滞的空间突然静止,迷幻感使人眼花。
林飞凝视着那月台与残留的夜雨,在料峭春寒中拢起衣领,暖意柔软地拥抱了下颌,他叹息一声,一大团潮湿的白色扑向空中,消散了。几周之前,秋季已降至树梢,树枝变黑,风变冷,天空在雨水不断的冲刷后已经模糊。
他握紧边角磨得熟烂的提箱,在衣领和帽檐之间无声地张望列车将来的方向,在那边,石块上漫漫地拉伸着钢铁的条纹,直至目不可及处,在远处晨光闪烁的一线上无迹可寻,好像没头没脑的顽劣山鬼在风里失去踪迹,却不尽明了前行的目的似的,而林飞明白极了,他要去找他的安眠,又或许什么也不明白。
在上一个月里,他有二十七天没能入睡,在蓝色玻璃窗包围的房间里长时间枯坐,或陷入沉睡一般的,无比清醒的谵妄,有一段时间他完全处于空白无意识的状态,就这样换了衣服,上班、填表、吃饭,直至在夜晚闭眼倒下,正如一个寻常男人一般稳重明智。
可是林飞心里明白,他没有睡着,不然为何在凌晨又一次打开了窗户眺望夜雾遮掩的灯光,又起身站在镜子前冲着睡梦中的自己摇晃手指,尝试判断是醒是梦呢?
秋雨来后,一天夜里,看到小指上长出了一截青苔的他吃惊地从床上跳了下来,接着低头看见墙的边边角角,图画书的每一个人头顶上,无不是细小而健硕的青苔,镜子里牙齿光滑的表面也变得粗粝,快被青苔攻占去了,还不算太迟,他认为他必须赶在青苔席卷之前离开。
在那最后一晚,由于扰人的忧虑,他穿着大衣,裹了毛毯,盖上被子之后,才甘心沉入那已经干枯的睡眠之沼。但那个晚上的凉意细丝般钻进了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林飞早晨刷牙时吐出了一大堆散发水草味的浅绿色泡沫。他愣在镜子前,心脏吃惊地猛烈跳动,好像草原上的一阵狂风,因为他看到了脸上绿色的胡茬,眼里绿色的血丝。这时闹钟忽然响了,他注意到周遭的一片死寂,伸手摆好了颠倒的闹钟。
凌晨两点。
看起来不甚分明……
或许是五点吧。他想。
他看看黯淡的天色,难以分辨,他拉开了蓝色的窗户,可是在雨中昏暗的天底下,怎么能看出什么是明,什么是暗呢?对面的居民楼的窗格有些亮着,有些黑洞洞的,谁还能做出分别?他想。
落雨的天空下,楼下的疯老头开始唱歌了,他在摇晃地画着圆圈,他点的篝火不怕这场细雨,可他并不是一只有规律地鸣叫的公鸡,林飞仍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他喃喃自语道:“我疯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所在,一个落雨的湿润房间里,一个将要被青苔吞噬,被罪恶吞噬的所在,即使这绿意只是在幻想的土壤上萌发,从这些苍白坚硬的残渣形成的养料里也长不出什么丰盈的罪过之果。
真是太过贫瘠了,过分干燥,这样的沙漠,在吸着我的血。这个可怜的人,满身的鲜血已化作一缕青烟,他是一颗滚烫的沙尘中即将消失的露水。
他是一个罹难者,然而除了人心本身的荒凉以外,没有别的磨难。虽然这片天空下满地的种子都不肯发芽,也是不足以视为罪过的,这也许是命运之类的东西吧?
难道我在为此忧虑吗?林飞想,我为何不能像别人一样沉沉入睡呢?
二十六岁的林飞回顾起他短促的人生,其无奈之情,就像一只肥硕的青虫点头数着身体简陋的分结,在这片现代城市的森林里,他无异于一只可耻的蠕虫。
天真的童年时期他与伙伴一同游荡在街巷,那里充满了来自现实世界的威胁言语,尽管在年长的人毫无顾忌地说笑中得到了很多关爱,残酷却隐藏在笑容消失后那一秒僵硬的嘴角上。六岁那年他隔着紧锁的防盗铁门,从铁栏间隙抚摸野猫的脊背,他为了取下挂在树上的风筝,耗费整整一个下午的时光,这一切都结束在喉咙变得沙哑的那一刻。学校圈养了一群困兽,因为他们别无去路,如果只身在外,社会既没有多余钱财来养一个闲人,家庭中也没有人能够提出足以安身的智谋,一家人只会终日惶惶不安,如此下去,恐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于是十六年的青葱岁月在两点一线里度过,到处宣扬着的自由与正义的鬼话,充斥着毫不费力,凭着热情就能兑现的理想,热情激动消退之后,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往前走,教师往往是不允许学生问到他们也不懂的深奥之处,只要他们满足于所谓基础的知识,所以他推测,故作高深的人们对于人生的意义,社会的进路之类,也全是不知道的。一切都丧失了神圣感,活着,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挣钱。尽管人们口中胡话连篇,他并不相信除此之外他们真的知道些什么事。
青葱岁月有理想,怀着赤子之心的年轻人们,很快便受疾风猛雨摧残,消沉了下去。眼睛里的火光熄灭了,身体肿起来,开始冷语相对。他们在大学里挥霍老一辈的钱财,享受着一种腐烂的生活,但凡娱乐,便涉及轻佻的愚蠢和情色,说说爱国,爱家之类的话便可糊弄作业,毕业后回到家乡,就可以做新一代的平民和庸吏。
而那些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行乞的人们,对于生活得还算不错的人来说是一种如野兽般狰狞的压力,如一股火烧燎着他们的心底:
“如果工作不努力,明天就会沦落到此地步啦,什么事都有可能,好事不必盼望着,坏打算可要做好。”
“就算多有能力和技巧,也别想着更好的位置,人脉把好事都锁住了,还是不要妄想吧。”
林飞亲眼目睹深圳工业区上班的蚁族,二十个稚嫩少年,同住一个狭窄的房间,他感到震撼以及恐怖,虽然经历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新时代的年轻人,仍然毫无尊严。
二十三岁时他回到家乡工作,与岗位和房产签下死契,埋头在数据的海洋里,每个月末便期盼着工资来填补一个个欲求的空洞,除此之外别无想法,身处如此平安无奇而碌碌无为的境况,已有三年了。
鲁迅曾在野草集中慷慨悲歌:“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而今眼前所有的,不是焦土烂泥,蓬蓬野草,又是什么呢,种子?种子又在哪里?莫非在心里吗?关于心的事谈了太多,却没有一件是真的,这不免使人感到绝望。一切能说的词语都被商业作践干净了,不免使人沉溺于沉默,在眼光与手心里表达最后的纯净真心。
茫茫夜色中,他用随性编造的曲调小声哼唱着太宰治在汽车后座上与他叔叔的对话:
“人间有什么呢?”
“人世之中,唯有色与欲。”
生活是一片沙漠,仿佛回想起了并非这一生曾有过的生活,林飞的头脑中满满皆是绿意,像酒气在蒸着思绪,他是不是疯了,是不是已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呢。到明天就他就再也不必去想,因为他就要离开。一切都遮上水汽,充满水雾,他是什么人,他也不会记得了,或许根本没有林飞这个人吧。
洞开的窗口将房间暴露在黝黑的天空之眼中,风涌进来,他仰视云中忽而闪过的电束,天空是如此空旷,气流带来了新的呼吸,他深吸一口气,把行李装进手提箱里,在门口系好靴子,掩上了房门。
他穿过阴暗的,石灰剥落的楼道,不小心触碰到了散发潮湿腥味的栏杆,手沾上赤色的铁锈,无边黑暗立刻就侵蚀了他的一角。
光漏过天空大片云朵的缝隙,一块一块地掉在昏睡的大地上,如深蓝色的海底在波动,行行树木伸展着黑色的骨骼,天空下水泥铺就的一条条道路,砌起的一栋栋楼房原本就落满了城市的灰尘,此时被雨点打得斑驳肮脏,光与影已陷入泥泞,终于城市变成了一整片灰色的平面。从天空俯瞰,仿佛一条干燥的灰色滩涂。林飞行走的渺小身影如一只泥鳅从那淤泥里滑过。
他站在一个空白的广告牌前,冷硬的金属表面上映出他的脸,绿色的胡须好像没有那么明显了,他呼出的气息弄花了他的影像,随着手指的擦拭,他脸上的各种线条就逐渐恢复了原来的黑色。
忽然他看到镜面上有一个亮点出现在身后,他转过身,看到那一点晨曦越过遥远的山脉,突破了凝固的黑夜,就像微微打开密闭的盒子,射进的光一样。
城市没有昼夜,时间是十分混乱的。他口袋里的表是三点钟,远处广场上的大钟是十二点钟,商城电屏上是八点钟,人们各自行走在不同的时间线,犹如行走于一个盒子里六个不同的平面,永远也不会相触碰,所以时间的一致性也并不要紧了,只要各自约好了便很好。
于是当他走向那一点晨曦的时候,就与晨曦约好了。手表指针缓缓地指向了清晨时分,六点半,同时乌云也渐渐退出,表的玻璃壳反射着那个光点,在雨的昏昏然里显得十分诱人,好像是枯死的树枝上新生出夺目的嫩绿叶片。
林飞提着行李箱,沿着通向城市外围的道路一路走到了火车将来的月台上。
覆满清澈水珠的黄色列车在雨后空气里飞逝,明快而鲜活,那锈蚀的阶梯好像也被洗干净了,在他的靴子下发出吱呀声,好像一片新生的苔藓。
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列车启动以后,窗口漏进来的风在轻轻敲打着帽檐,他向右一瞥,看见一只雨后垂死的飞蛾在汩汩水流的痕迹里微微颤抖着,说不清是风吹,还是它残存的生机。浅色的水痕像一只只憔悴的手指,在窗上划下悲叹的指印,看起来仿佛发生着一场正为风声呼啸淹没的掠夺。
林飞心里一颤,窗外又沥沥落下雨水,空中,墨蓝的乌云迅速挤过来,惊人的聚汇使远处一只在围墙上瞌睡的老猫受惊逃走,但天空却被郊外透明柔和的景物围绕,仿佛是沉默中萦绕着温柔的音乐。林飞乘坐的鲜黄色列车显得很扎眼,不动声色地飞速奔驰,林飞凝视着桌上杯中晃动的水,手指徒劳地轻轻敲打,想捕捉震颤的频率,路途十分颠簸,他的四周都晃动起来,稀疏的几名乘车所发出的嗡嗡交谈声,靴子砸地声,擦肩摩挲声,都被脚下铁块的轰响遮盖,仿佛沙漠里上升的热气一样,让神智再清醒的人也都摇摇晃晃,他背后的大汉在这致命的摇晃里使劲地打起鼾,和死神签下了短暂的契约,在这十几个小时里,无论世上发生什么,都无法影响他分毫,然而林飞不会有这样不幸的安宁,他仔细感受着脚下空洞的地板,背后粗糙的,有些腻的坐垫,平凡如常的一切已经在他布满血丝的瞳孔里得以升华,林飞想到,岁月流逝好像是在不停地滑下不幸的深渊,自己却可以清楚地看着痛苦的石块和大风以何种方式把自己击碎,不放过任何的细节,而他们的生命却似乎在黑暗里一点点消失枯萎了。
他在这样的遐想中将近陷入了虚假的昏睡,他的意识像傍晚大海上的夕阳,无限逼近了黑暗,但是总有一丝光线漏出来,隐隐约约处好像还有一队挣扎的船桨在噼啪作响,失眠的聒噪也似乎永远也不会再消失。
永远有多长呢?他想,如果流逝的东西总是不能洗去将要停止的嫌疑,那么永恒的其实是每一个瞬间,就像车窗的窗框,他扭头注视着黄昏的天空,窗框把他和外面的景色一帧一帧地映下,像恶毒的琥珀包裹着苍蝇,每一个凝滞的瞬间都停止了呼吸,将会永远留在那里,林飞恍恍然用手指去擦着远处房屋发出的灯光,时光的留影通通被火车甩在了后面。
四周忽然黑了,列车驶进了隧道。转瞬间点点灯光又重新在视野里跳动起来,棕色的墙壁吞噬着风,把风咬得残缺不全,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林飞嗅到窗缝里有血腥的味道,神经被出其不意地刺痛了一下,随即发现刚刚漆成鲜黄的车厢其实已经老旧,风雨夹杂着锈蚀不断向车内部渗漏着。
他身侧传来呜呜的声音,刮擦的呻吟,那是车厢在隧道大风的挤压下发出悲鸣。雨夜更猛烈地显现出征兆,像是要把大山掀翻一样,猛扑进这条狭小的通道。
车身的这股震颤使很多人都醒来了,各自恍惚地慌张四顾。
林飞却想到:
“宿命使人清醒的惩罚,是怎么都不够啊。”
林飞出于一种怜悯去寻找玻璃上那只飞蛾,不出所料,弱小的虫子葬身风雨冲刷,光滑的玻璃窗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驶过那条隧道之后,外界却再次落入黑夜,火车在黑夜里顺着细长的铁轨行驶得越来越远,黑色越来越安静,在轻微的雾气与一点点光的构造下,天空与暗暗涌动的风重现了远古广阔的黑暗安宁。
在这片黑暗的寂静下,他还是清醒得很,没有一丝睡意。林飞想,一个不知道明暗之分的人是不会睡着的,于是他静静坐在漆黑里思索,却没有头绪。活人怎么能明白死的事呢。通常人们不会经历真正的黑暗,闭上眼睛,眼睛里还残留着光,有人能看到更多的色彩和影像,跑跳变换着。光不曾离去,黑暗与时间一样是由规则的刀所裁剪出来的生命片段,当生命很模糊时,就会失去时间与明暗在自己身上投映的清晰的轮廓。
不过此时林飞陷入了真正的黑暗,令人嫉妒的安静,拂去了天空中所有的尘埃,只有清澈的星星,浮浮沉沉,世界不说话,他的心也不说话。他不需要明白什么,他由混乱而彻底失去了一切,这可好啦,没有时间,也没有昼夜,这使他的心清醒爽朗,他忘了他是谁。
他坐在黑暗里,火车飞逝着,他什么也看不见,周身涌动着风,他好像坐在一座旷绝独立的山丘顶上,在风里遨游。
在世间,脆弱的明与暗支撑着人们的生命,有些人依靠光荣活着,有些人依靠黑暗活着,一旦抽掉那根脆弱的支柱,他们就会破碎倒塌。因此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捍卫着不容侵犯的信念,多余的自尊心产生了数以亿计的孤独破碎之心,但缝隙里的黑暗其实是很温柔的。虚无永远不戴面具,因此它没有表情,不会屈从天使或害怕死神,它是所谓的安宁。
林飞掉进了那虚无的缝隙,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一样快乐。
不久后他再次回到阳光下,他和车厢里的每个人交换了一个秘不可言的微笑。
窗外是阳光下的群山,不断地闪过,光在水杯和手指间像一尾鱼似的来回游移。
他对面带着黄色帽子的男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因为林飞没有拒绝他的目光,与他对视着,对面的黄帽子已经被阳光打湿了一大半,后面的走廊也缓缓地浸泡在阳光里,随着车厢左右抖动,空气被烘得很温暖。
黄帽子的男人可不是一个想要塑造角色的演员,但他使劲跺了一下脚,边吃瓜子边不停地左顾右盼,稍有不舒服就会咳嗽,身体在极为特别的轨迹里出人意料地扭动着,如果在一部什么电影里,人们准会想到他在给什么剧情打铺垫或者费力地表现自我,可他没有任何目的,他只是一个林飞再也不会见面的陌生人。如果另一个人能把自身抹去,演得像他,那么准会成为为人传颂的高超绝伦的表演大师,可是没有谁在表演,生活是如此的赤裸,流失在残酷的时光,不怎么美好,不堪歌唱。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每个人都很逼真,光彩夺目,这仅当他是个被周围抹去的灰色小角色时才有可能,一旦把人放进目的里,他就会扭扭捏捏,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如果谁也不能够像这样偶尔仔细看着别人,最后人们就会相互失去了。
黄帽子男人咔一声向上推开了车窗,将窗卡住,风涌进来,像一股水,其余更多地向后涌去,带来了阳光的气味,从那一角开始,火车里翻涌起山里阳光的暗香,林飞的心一颤,他几乎要醉了。他把手指浸在窗口流淌的风里,感到它事实上具有水流般的劲涌的形状,被窗口切割之后,像是遇到河里的轮船似的分流开了,他把手掌贴上去,就能摸得到激越的水面。
我是第一个发现风的人。他想。在过去曾有过第一个发现水的鱼,是那只鱼变成了人,而我需要变成些什么呢?我顶多能够离开水面,奋力地挺身一跃,又再次跌落。那就把水面砸个粉碎吧,他愉快地挥了挥风里的拳头。
这样想着,他第一次短暂地离开了阴郁遮蔽的角落,两只眼里连着瞳孔的锁链都被切断,锁链另一端连着的人眼破碎如同灰尘,被这风洗去了。他眯起眼睛适应窗外的阳光,看到那无边无际的光,仿佛振翅翱翔的鸟,光阴隆隆的轰响声充满了天地间,如果有什么能够形容这样神圣美丽的光景,那么就只有天使了。他的心潮涌起,与外面的光相拥融化,砰砰地撞在海岸的大石上,洁白的泡沫膨胀而后破碎,窗外的水迹如光影似的飞溅到他的手上。
看哪,那纯洁新鲜的绿色原野,像一股水流洗濯着他眼里每一线光,每一笔都抹上单纯的色彩,黄色的稻草人伫立在路旁,青绿的荷花塘上略过灼目的一点深红色,这份单纯明丽无限地向两边伸展,触手可及地铺在铁轨的两边,一直铺到与山麓的阴影交接的地方,突然就晦涩起来,那暗处是一些褐色的小路,一些农人背负的铲子和锄头正在空中起起伏伏,小楼栏杆上搭着一条条暗淡的布块。
上方是一连串褐色的高山,在蓝天清澈的背景之上,完好地显现出毛毡一般的质感,光秃秃的,非常可爱,犹如马的脊背,让人想轻轻地爱抚。
天空上浮动着巨大如鲸鱼的云朵,一路留下的影子覆盖着大山随时滋生的欢喜。
林飞出神地看着,他身后妇人怀里的小狗却不安地冲着他伸了伸鼻子,即使他衣服穿裹得很严实,鼻子湿润的幼犬仍然嗅出了他潮湿的灵魂。
因为阳光遍野明快已极,一切就将停滞不前了。
不知道是在哪一秒,从鞋子的微润,到全身冰凉,耳朵里灌进了嗡嗡的蓝色,被包裹,托起,一阵昏暗过后,在黑暗里撕开了刺眼的出口,他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漂浮在水中,像子宫里的胎儿一样悬挂在这个被车厢所隔离出来的小方格里,水杯浮在桌子上方,像水草一样摇摆着,许多歪着脑袋,姿势扭曲无力的人,大大小小的拖箱,不同形状的鞋子,变成了好奇的鱼在这团凝固的暗蓝色里不紧不慢地游泳,所有能看见的东西都漂浮着,失去了原来的光彩,尽数染上暗蓝色的光衣,车窗外一片虚无的漆黑。
林飞安静下来,终于合上了眼睛,也许我醒来时会在床上,他想。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gdnyy.com/wadwh/1283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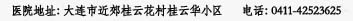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