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静nbsp苔藓火车amp女
唐小静女80后教师河南禹州市人
有小说散文见于《牡丹》《原野》《警界参考》《鉴湖》《奔流》《新疆文学》等刊
苔藓火车
火车穿过卜兰镇,远远地把它抛在身后,带着某种遗弃性质的逃离,我离开了这个灰扑扑的小镇。
没有人知道我来过,你自然也不会知道。我甚至没有去你栖身的地方看一眼,我想象不出它的样子,是像个小馒头一样聚拢的坟丘,还是平坦散漫的土包,或者是公墓群里规整如仪仗队一样的水泥墓碑,可是即便我与你近在咫尺,又能怎样?我依然是那种曲缩成团的性格,就像当初我的离开,我只是不愿意去面对。我的抗争和懦弱历来都旗鼓相当,我几乎一次也没有战胜过它,它在我体内饱足生长,像一个肥壮的虫子,我讨厌它,可也拿它无可奈何。
你的事情是邹小丽告诉我的,这个女人的面容我已经完全认不出了,她的脸已经成为整容流水线的模本,她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有钱人,她的话依然碎且多,瓜子皮一样扫不净。可是有一句却困住了我不耐烦的脚:“你知道吗?祁侠死了!骨癌!锯了一条腿也不管用。”
火车穿过密集的隧道,世界我眼前明明暗暗,催眠般循环往复。我的记忆里伸进一束追光,在强光下,一切都无所遁形,甚至纤毫毕现。
十六年前,我们三人也曾乘坐这样的绿皮火车,那时的青春取之不竭,你坐在我对面,我和于梁坐在一起,一路谈笑、打牌、看风景,快乐像奔突的泉水。火车上的人稀稀拉拉,我和于梁会趁你下站台或上厕所时吻一下,带着偷情般的刺激,可是这厢吻刚脱唇,抬头却见你眼水晶亮地看着我们,“于梁,比赛吃毛蛋咋样?”你剥开一个,那内核已初具胚胎状貌,透明的躯体被一层霜翳般的薄膜包裹,里面有蜿蜒的血蛇,你的嘴角带着一丝逞强的笑,悠悠然地把它塞进了嘴里,“怎么样?是男人就来一个!”于梁打趣你:“男人吃毛蛋为壮阳,你吃毛蛋为哪般?”其实那时我已经和于梁在一起了,我想你也看出来了,所以在随后不久恨恨地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你?我不是一个习惯把内心所有都宣之于众的人,坦诚不是我的标签。
可是现在我要向你坦诚的是,我们的三人行,除了你的主动请缨,还因为你总是泛滥无度地夸我,这让我在于梁面前颇有面子,所以我乐于带你。并且我知道,于梁对你不感兴趣,这让我觉得相对安全。没有几个男人会喜欢你这种野气横生的女孩,我这点卑劣的小心思在我的感情史上屡屡作案,那时就害得你成为群嘲的对象。她们笑你是瓦数超大的灯泡,你也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的确,你很强大,热带雨林般的性格体质一度让我钦羡,所以,我至今还恍惚,我是不是辗转在梦里,你真的死了吗?
可是邹小丽红口白牙地说你死了,她说得时候没有丝毫情绪,就像在说今天又堵车了一样稀松平淡,她和我们不是一类人,从前不是,现在也不是。并且我发现,一开始不喜欢的人,过去了很多年,就算经历人生磨折,喜欢的东西会变,可不喜欢的还是不喜欢。
你同样鄙视并厌弃着邹小丽,当年你曾痛心疾首地质问我,邹小丽甩掉的咱再捡起来,有意思吗?再说了,能跟邹小丽那贱人好的,人能好到哪去?你说这些话的时候额头的疤痕一跳一跳的,好像在跟随着你的情绪律动,那疤痕是你自己拿砖头拍的,血流出来的时候,邹小丽和她那帮兴师问罪的死党都作鸟兽散,之前她们还扯着我的头发,说我是婊子养的贱人,专爱抢人家男朋友,你用惨烈的方式护住了我。我抱住了你因疼痛而颤抖的身体,伤口在卫生纸上洇出夺目的红。我的眼泪涨了潮般汹涌,你拍拍我,说这妮子不地道,不震她一下她没完没了。果然邹小丽再没找过我的麻烦。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那时我已沉醉到和于梁在一起的感觉里,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怎么喜欢他,总觉得上了大学不谈点恋爱就可惜了,虽然我们只是些自考的散兵游勇。虽然他和我一样附生般被动,可是一旦和他发生了亲密关系,我就越来越依恋他。我们把夫妻间该做的事都做了,只差没生个孩子了。
火车停了下来,在中州站稍事歇息,这行将老去的机器是喘着粗气工作的。站台上的小贩都云集过来,卖肉夹馍的、糖葫芦的、咸鸡蛋的、各种饮料的……旅客们有的舒展着筋骨,踱到站台上抽烟解乏,有的提包挈箱,怀抱着回归之喜消失于人潮。我忽然觉得,中州站是我的目的地,我要回到广海路商学院的宿舍里,那宿舍老旧阴暗,我们常常躲在楼梯口吓人。我甚至看见了黑暗中你窝藏的身影,听到了水房滴滴答答的响声,以及室友们来回踩踏的脚步声……或者,我要回到王寨村里,那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各种夜市小吃夹道横塞,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爱情的小窝。
十四年前的王寨村,许多小饭店、棋牌室、一元店、夫妻用品店、黑诊所杂陈其间,各色自以为牛逼却猥琐的人分布散落在各个角落。各种人间乱象聚结于此。警车常在这里轰鸣而来,喧嚣而去,看热闹的人们像鸽群抢食般簇拥围拢,一会又四散开来,留给人们一片短促的谈资,我和于梁就租住于此。那里的生活成本低,炸串一毛一串,配个烧饼才一块钱。肉丝面一块五一碗,可以吃到撑。那时我们经常在这种小馆子里吃饭,你和于梁老是争着付账,你早早就打零工赚钱了,手头比我们宽绰。那时我以为幸福不过如此,无序拥挤混乱在我眼中却是缤纷可亲的市井气息,我甚至一度爱上那里的不堪。即便让我和于梁终生蛰居于此,我也乐意。那时候我们常常站在筒子楼顶层,看纵横交错的电线,看熙来攘往的人群,看着看着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穿过大门,我们就知道你来了。那时你常来蹭饭,我们常搭伙做一种番茄鸡蛋捞面,面煮好过水,番茄炒酱,加洋葱蒜薹,码上黄瓜丝,泼上蒜汁,淋点芝麻酱,色泽喜人,吃起来也清爽。考试前,我们三人就一起去八角楼里复习。
你是否还记得那一晚?我们喝了啤酒吃了螺丝,你脸色酡红,突然涎皮赖脸地要求留宿,小屋酷热难挡,我们就把凉席铺到了楼顶,起初三人像聒噪的蛐蛐,后来你渐渐没了声响,风在耳边旷荡,你的鼻息渐渐沉稳。于梁突然兴起,我们就在你侧卧的身后悉悉索索地做爱,无耻又无畏,那真是一段快乐又堕落的日子!那些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化身一场场性爱的雨,淋漓飘洒在年轻的身体里。明天权且不想,只耽溺于这最原始的欲望。第二天的你不知是否察觉到什么,半痛心半戏谑地用手支起我的下巴,拖着长腔念白:可惜了!可惜了!纵然生得好皮囊,便宜了那四眼于梁!我笑骂着去追你,心里又有一点羞赧,你夸张地叹口气摇摇头,背起帆布大包,跑了。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毕了业,找到了工作,然后买房结婚生子,扎根在了中州市,你的轨迹也和我们并行不悖,我们熟知对方的生活方式和一切人生细节。我们会经常聚个餐唱个K,你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甚至我们可以结为亲家,这些画面被我们口述和脑补了很多次,那时年轻笃定,觉得命运已一手在握。却不知,它已经恶意分叉。就像这列火车还是会开走,中州站说到底不是我的目的地一样。
火车进入丛林带,轨道像一条中分的发缝,最近的时候,我的手可以捋一把叶片,像怀揣心事一样把它藏入口袋,等它慢慢枯萎干涩,化作齑粉,风一吹无影无形,它的荣枯记忆也一并化为乌有。就像此刻的你,肉体同记忆沤烂在泥土里,而我却要背负着它继续前行。
人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会格外执着揭秘,那是勇敢者的游戏,比如你。可是我却一走了之。表面上我早已忘却并解脱,我的散缓的人生好像并没有因此而饱受影响,可是我的胸膈间却食而不化地藏匿了一段陈年公案。甚至一度影响到我的消化。
那天的事像手工上色的照片,鲜明却失真。以至于我常常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并把它和梦境混为一谈。就像现在怀疑你的死一样。说不定一个激灵醒来,你和我又活在不同的空间里,各自忙着手边的事。死亡不过是岁月深处迎候你的接站人。
我像往常一样从坐着火车,从中州站下车,回到王寨村,带着老家盛产的酱牛肉,风湿热稠密,估计一会暴雨将至,我满心欢喜地期待一场极端天气,我们三个可以喝着啤酒就着酱牛肉,看外面粗如白链的雨。享受着蜗居里紧实细密的快乐。
我给你的呼机上留言:我已下车,给你们带了酱牛肉。一会见。
我甚至还想象了小别后欢爱的浓度,身心激荡在回归的路上。
你曾经不解地问我:“男人真的有那么好吗?”我诡秘地笑笑:“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可是跟一切狗血俗套的桥段一样,你试了他,或者未遂,我已不得而知。
钥匙转动完锁芯,门欲开时,发觉被里面的褡裢反锁了。屋里撕拉扯拽的声音让我心慌,意识开始乱舞,预感像暗处蜂拥的飞蛾。扑面而来。
屋里好像就你一个人,我第一次以审视的姿态看你时,发觉你身材挺不错,腿修长挺直,肌理细腻光洁,锁骨像一扇振翅的蝴蝶,你的眼睛里泛着青瓷一样的光,你坦然自若地和我对视,好像羞怯是留给我的。你指着窗口,态度不逊地说,你男人跑了!我挥起手打了你的脸,揪掉了你几撮头发,又挠了你一脸血痕,像泼妇一样用最脏的字眼骂你,但我又一度恍惚,这段暴力戏码是否是梦境产物?我因不解和愤恨无处宣泄,在梦里找到了出口,我无法证实。
我从筒子楼里走出来,头有点晕,那一天的雨没有如约而至,空气依旧燠热难当,我走出街口,只觉得耳间嗡鸣,一辆救护车抬了担架匆匆往里走。后来知道,那担架是抬了于梁,这个怯懦和性欲一样多的人。在你开门的一瞬选择了跳窗,一楼的高度决不至于使他出事,他只是被一截老化的电线击倒了,这闹剧没有变成彻底的悲剧,于梁没有死,但是很多年以后,你死了。
我在小诊所里买了安眠药,我绝非想死,我只是想让自己沉睡,用睡眠去过渡这一段不堪。我在小旅馆里过了几天暗无天光的生活。醒了吃,吃饱服药继续睡。预计三人共欢的一块牛肉,被我啃食殆尽。
清醒后街道上已经暴雨成河,没腿深的雨水冰凉地刺激着我复苏的神经,我买了返家的车票,扎根在老家,也是家人祈愿已久的。我一个人度过了悲哀反刍期,之后很快工作结婚生子,日子平铺直叙,你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出,你留在了中州,在一个宾馆里做到高管,却一直单身。别人风言风语提起你的时候,总有暧昧的目光游移到我脸上。那是隔了多年依旧兴味不减的八卦心。真不知当初我们做了他们多久的热闹谈资。
我也曾经穷思极想你的动机,难道你察觉了我的心思,不甘心做陪衬所以刻意报复?还是你对于梁早就心有别样,或者只是单纯地想要尝试一下男人而已,所以挑了最近的下手?或者你就是想让我看清于梁的实质,所以不惜以身试法?一切说辞都饱满有理,却又都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曾反复论证,但结果也不过是越证越乱。
我是在前天收到了你家人邮寄的包裹,地址是我的娘家。里面有很多我用过的东西,包括钥匙扣,旧的准考证,一元店里淘的发卡……经过光阴的浸渍都变得斑驳老旧,唯有一个吸水鸭的毛绒玩具,还是簇新的模样,我惊奇于你如何使它逃过时间之手,捏捏它的翅尖,里面传来一阵声波干扰般的噪音,再往下听,清晰又模糊地传出了一句:对不起,我喜欢你。
时间是真相的宿敌,像干涸的河床终于显露出河底的风光。
火车即将驶进我的故乡,这是它最后一站,也是退役前最后一班,列车员语带煽情,对这暮年故友恋恋不舍。车窗外,田畴河流坡地都匆匆而过,余晖遍洒,亮烈如血焰,温暖中又带点凄清。我闭上眼睛,车轮仿佛永久停滞,时间和时间撕扯胶着,直到我的脚下长出藤蔓,布满苔藓。
(完)
女人初心
前言:泰坦尼克号结尾,老露丝说:“女人的心是一片秘密的深洋……”的确,女人的心是厚腻乌沉的海水,有阳光也无法穿透的幽暗,似乎难以捉摸又无迹可寻。实际上,女人的心既是神秘的海,也是清浅的滩。既深不见底又一览无余。
公元年,王映霞面对着镜头,用略带软糯的杭州官话娓娓道出:“我所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与他性格不同。”
尽管岁月侵袭剥蚀,92岁的王映霞眉目间仍依稀可见当年“杭州第一美人”的风采:肤色白皙衣饰雅洁,更有一种千帆过尽后的从容恬淡。
把时间拨回到年1月14日,王映霞19岁,已是一个丰满腴丽鲜妍明媚的少女,自身所发散出的熠熠华光,刺射了郁达夫阴郁的双眼。从此,郁达夫对她一见倾心穷追不舍。
作为一个不谙情事的19岁少女,郁达夫吸引王映霞的无非是作家的光环和其潇洒的气度,当然还有郁达夫追求她时不顾一切地炽热疯狂。
少女的心总是善于织梦的,面对一个已婚男人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的灾难式攻势,任是再理性的女子也招架不住,于是王映霞缴械投降了,当然,切断王映霞退路的还有郁达夫那率真露骨的《日记九种》,记载了他们恋爱欢好的细枝末节。包括何时表白,何时接吻……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把情事大白于众的做法不啻于一颗惊雷,人们在震惊的同时,也想观摩一下大才子是如何虏获美人的。王映霞虽怪其孟浪,却也无可奈何。懊恼羞涩又甜蜜地投入到这段让她花开欢喜的爱情里。
才子佳人的戏码演绎至此,戏台上就会拉下帷幕宣告结束,底下观众都会带着余味去脑补神仙眷侣的美好生活,的确,在最初的几年里,两人的浓情蜜意一直都是如影相随的,花前谈心月下散步,事无巨细滴滴点点都是要密语绵绵的。王映霞不善烹饪,郁达夫就带着她一家馆子接一家馆子地去吃,久病成医久吃成厨,终于王映霞可以自如游刃于刀案锅勺间了。
起初王映霞也待他极好,把家务和收入打理地井井有条。还总是炖上一锅浓酽的黄芪老鸭汤,以期治好他的肺病。在她晚年回忆这一段生活时,字里行间温情毕现: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可是在爱情的浓度渐渐被生活的庸常所稀释,郁达夫作为作家的神秘感也慢慢消弭殆尽,他性格中潜隐的缺陷一一凸显:嗜酒、敏感、多疑、动不动地离家出走和与前妻的藕断丝连。虽然也是名士习气率性而为,可真过起日子来,却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此时的王映霞应该还是爱他的,他毕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那轰烈浪漫遐迩皆知的情事也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跟着这样的大才子大作家,享用他才气名利的同时,也得忍受与他才气并蒂连生的诸多缺点。当神仙眷侣堕入凡尘,所面对的也无非是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辛苦琐碎,再横溢充盈的才华再如雷贯耳的称号都显得苍白无谓。不知道王映霞在屡屡看到烂醉如泥的郁达夫时,会不会对委身于这个任性疏狂的男人感到无奈和后悔。王映霞在自传里曾引用曹聚仁的话:“诗人如果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子,诗人如果住在你家的楼上,他就是个疯子。”
于是罅隙在虫吃鼠咬的流年岁月里慢慢变大,直到成为不可挽回的裂痕。
王映霞骨子里应该是个爱繁华热闹的女人,女人的虚荣当然也有,而郁达夫则惯于独处懒于社交。于是能言善饮风情有味的王映霞就成了“风雨茅庐”的代言人,眼波流转间旖旎万般,丰肥的体质配上醇熟的情韵,自然招来了不少裙下客,出轨与否因岁月迢迢,相关人等均已作古,无确凿证据而尚无定论,但暧昧一定是有的。女人的出轨,除天性放荡外,最大的原因无非是对丈夫失望不满,此时的王映霞对郁达夫已经哀怨丛生了。除了上述所言,还包括郁达夫频频以妾称谓她,并没有达成郁当年的承诺(三年内若没与原配离婚,就自杀),郁达夫将浪漫激情全部投注在了恋爱和蜜月阶段,这种汹涌恣肆如火如荼的爱,太容易和此后的平静冷淡形成落差,于是王映霞曾在信中不无幽怨地说:“别人都会在文章中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哪怕王映霞曾一度想去福建陪夫,都被郁达夫拒绝,因为他要维护他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放旷。
于是,“风雨茅庐”就真的成了郁、王婚变的风雨之地。
《毁家诗记》的发表彻底撕裂了夫妻间残存的缀连,郁达夫在展现他文采诗兴的同时,也把王映霞塑造成一个拜金慕贵纵情任性的女子。他的“暴露癖”至此也达到一个顶峰,极端的性格使他对待王映霞的态度有着云泥之别,爱时捧之为仙恨时毁之为鬼,当初恋爱时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如今分道扬镳了也事无巨细地大白于天下。自虐及虐人恰似一把双刃剑,伤害了王映霞的同时,也刺伤了他自己。
王映霞在晚年回忆她最后离开新加坡时说到:“我离开郁达夫,拎了一只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郁达夫也不送我出来,我知道他面子上还是放不下来,我真是一步三回头,当时我虽然怨他和恨他,但对他的感情仍割不断;我多么想出现奇迹:他突然从屋子里奔出来,夺下我的箱子,劝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变了……”
而这厢,郁达夫面对王映霞的离去,声泪俱下地对友人控诉:“她真的变心了!头也不回地走了……”而他不知,王映霞举步维艰地回了多少次头。
无论怎样,错失的还是错失了,能失去的就不必再回头,能回头的就不会失去。谁能保证他们和好后不会再度决裂?
于是年4月4日,王映霞风光大嫁,与钟贤道举行婚礼,按她自己的话:“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室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钟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
三年后,郁达夫被害于苏门答腊岛,尸骨无存。
钟贤道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在与王映霞生活的38年时光里,他温火慢煨的爱贯穿始终。他们的女儿钟嘉利曾说,父亲在写信时就称呼母亲为“老心肝”,从这称呼里,钟贤道对王映霞的宠溺可见一斑。王映霞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女人初心,无非如此,清澈明晰,一份踏实的爱,不折腾,不闹腾。如静水流深,虽无惊涛狂澜,却恒定永久。
咫尺天涯唐小静联络:
邮箱:
qq.北京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效果好北京治疗白癜风医院哪家好转载请注明:http://www.gdnyy.com/wahl/515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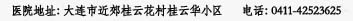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