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middot策兰痛饮某种虚空
湖南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zjdy/171025/5789682.html
保罗·策兰
(-)保罗·策兰,二战以来影响最大的德语诗人,年,其成名作《死亡赋格曲》震撼德国。年,策兰获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他的作品备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等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推崇。策兰生于罗马尼亚旧省北布科维纳首府切尔诺维茨(今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父母二战期间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本人战后辗转定居法国,在流亡中背负历史记忆的重压继续生活和写作。年4月的一个深夜,策兰在巴黎投水自尽。评论家乔治·斯坦纳称策兰的诗为“德国诗歌(也许是现代欧洲)的最高峰”,哈佛大学教授、诗评家文德勒称策兰为“自叶芝以来最伟大的诗人”。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他被公认为继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今天小雅带来由黄灿然老师翻译的几首保罗·策兰的诗作。雅众也即将出版黄灿然老师翻译的《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你的手充满时辰你的手充满时辰,你走向我──而我说: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于是你把它轻轻提起来放在悲伤的天平上;它比我还重……他们乘船到你那里把它变成货物,然后把它拿到欲望的市场摆卖──你从深处向我微笑,我从那仍然是轻的位置上对着你哭泣。我哭泣: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他们拿出海里的盐水而你给他们鬈发……你低语:他们正用我来充满世界,而我在你心中仍然是一条凹陷的路! 你说:把岁月的叶子放在你身边──是你走近来吻我的时候了! 岁月的叶子是褐色的,而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白杨树白杨树,你的叶子向黑暗里闪耀白色。我母亲的头发从来不是白色。蒲公英,乌克兰是多么绿。我金发的母亲没有回家。雨云,你徘徊在水井上空吗?我安静的母亲为每个人哭泣。圆圆的星,你绕起金圈。我母亲的心被铅穿裂。橡木门,谁把你拆离你的铰链?我温柔的母亲不能归来。羊齿草的秘密在剑的穹窿里影子们那颗绿叶色的心望着它自己。锋刃明亮:在镜子前谁不徘徊于死亡? 这里壶中也有一种活着的悲伤被祝酒: 它在他们喝之前花朵似地暗下去,仿佛它不是水,仿佛这里它是一朵雏菊,被要求给出更暗的爱,一个为那寝床而更黑的枕头,和更浓密的头发……但这里只有为铁的照耀而感到害怕;而如果这里还有什么亮起,但愿它是一把剑。要不是镜子招待我们,我们就不会喝尽桌上这个壶:让它们其中一面在我们叶子般碧绿之处破裂。来自骨灰瓮中的沙遗忘之屋绿如霉菌。在每一道吹风的大门前你那个被砍头的吟游诗人变蓝。他为你敲打他那面苔藓和粗糙的阴毛做的鼓;他用一只溃烂的脚趾在沙中追踪你的眉毛。他把它拉得比任何时候都长,还有你唇上的红。你把这些瓮充满并滋养你的心。最后的旗帜一头水彩猎物在灰暗的边界被追逐。所以请戴好面具并把你的睫毛涂成绿色。那盛着昏睡的弹丸的碟子被端到乌木桌上方: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葡萄酒在这里冒泡,一年多么短,这些神枪手的代价多么炽热──陌生地方的玫瑰:你迷路的胡须,树桩的慵懒旗帜。吠叫和乌云!他们正把他们的疯狂骑进蕨草! 像渔民把鱼网投进雾气和鬼火里! 他们把绳子套在头冠上然后邀请我们跳舞!并在源泉里刷洗号角──从而学习那引诱猎物的叫声。你选择什么斗篷,密度大吗,能藏住发光吗?他们绕着树干潜爬如睡眠,仿佛在提供梦。他们把一颗颗心猛掷上高处,一个个长满苔藓的疯狂球体:啊水彩羊毛,我们在高塔上唯一的旗帜!在樱桃树的枝桠里①在樱桃树的枝桠里一声铁鞋的嘎扎响。夏天为你而从头盔里溅出泡沫。带有钻石距②的灰黑色布谷鸟把它的形象画在天空的大门上。没戴帽的骑手从树叶间耸现。他在他的盾牌上显示你微笑的黄昏,那微笑已被钉在敌人的钢头巾上。梦想者的花园已应允给他,而他已准备好长矛,让玫瑰可以攀缘……但那最像你的人赤脚穿过空气来了:铁鞋搭扣在他纤细的手上,他在整个战斗和夏天里睡觉。樱桃正是为他而淌血。①过去的历史渗透现在的自然风景,前者有多暴力,后者就有多强烈。布莱希特曾在一首叫做《灌木丛中的独臂男人》描写过一个类似的环境:一个战争幸存者在捡柴枝,当他举独臂想感觉一下是不是在下雨时,忽然想起纳粹的举手礼。②距是指鸟距。宴会让黑夜被排出诱惑的高椽中的长颈瓶,门槛被用牙齿犁开,暴怒在早晨之前被播下:这里一片苔藓也许会为我们而猛长,在他们从磨坊那里来 为他们缓慢的轮子寻找安静的谷物之前……在那分泌毒液的天空下一定会有更多的淡黄色麦杆,梦也一定铸造得比这里更不同,这里我们为了快乐而掷骰子,这里遗忘和惊奇在黑暗中互换,这里一件事情计算一小时,然后被我们在狂欢中吐唾沫,装在明亮的钱柜里扔向窗口的贪婪之水──:它在人行道上爆破,为了荣耀云彩。然后把你自己裹在外套里跟我一起爬上桌子: 谁还能睡觉除了站着,周围环绕着酒杯?我们还能为谁喝我们的梦如果不是为那缓慢的轮子?法国之忆和我一起回忆:巴黎的天空,那朵巨大的番红花……我们到卖花姑娘的摊子买心,它们是蓝的,它们在水里开放。我们的房间里开始下雨,我们的邻居进来,勒松先生,一个瘦小男人。我们玩牌,我输掉我眼睛的虹膜;你把你的头发借给我,我也输掉了,他打败我们。他穿过房门走了,雨跟着他出去。我们是死人,而且能够呼吸。夜之光线一切中那最光明的,焚烧我黄昏爱人的头发:我给她送去用最轻的木材做的棺材。浪潮绕着它汹涌就像绕着我们在罗马的梦床;它跟我一样戴着假白发粗声粗气地说话: 它像我允许一颗颗心进来时那样说话。它懂得唱一首法国情歌,那是我秋天作为旅客停留在晚地①给早晨写信时唱的。那口棺材是一条好船,用感情矮林雕刻而成。我也驾着它漂泛在血流下游,比你的眼睛还年轻。现在你年轻犹如一只鸟跌死在三月雪中,现在它飞向你,对你唱它那首法国情歌。你很轻:你将在我的整个春天里睡觉直到它结束。我更轻:我在陌生人面前唱歌。①晚地,或迟地,策兰虚拟的地名。从我到你的岁月我哭泣时你的头发又一次飘扬。带着你眼睛的蓝色你铺开爱的桌子:一张夏天与秋天之间的床。我们喝某个人酿的酒,既不是我也不是你也不是第三个:我们痛饮某种虚空和最后的事物。我们望着深海镜中的自己并更快地把食物传递给对方: 夜是夜,它以早晨开始, 它把我放在你身边。赞美遥远在你眼睛的源泉里生活着疯海渔民的网。在你眼睛的源泉里,海恪守诺言。在这里,我,一颗在人类中居留的心,脱去我的衣服和一个誓言的光泽:在黑中更黑,我更赤裸了。只有不忠我才真实。我是我我才是你。在你眼睛的源泉里我漂流并梦着猎物。一个网捕住一个网:我们在拥抱中分离。在你眼睛的源泉里一个被绞死的人勒死绳子。整个生命早晨之前一个小时半睡的太阳们蓝如你的头发。
因为它们生长如一只鸟儿墓头的青草。因为它们也受到我们梦中在欲望之船上游戏的诱惑。因为匕首在时间的白垩悬崖上等待它们。深睡的太阳们更蓝了:你的头发仅与它们相似一次。像夜风,我在你姐妹可出售的怀抱里暂停;你的头发从我们头顶的树上垂下来,虽然你不在那儿。我们是世界,就像你是大门前的一丛灌木。死亡的太阳们白如我们孩子的头发:他从波浪里升起,当你在沙丘上搭你的帐篷。 他拔出快乐的刀眼睛无光向我们胡乱挥舞。黄灿然
诗人、翻译家、评论家。著有诗集《我的灵魂》《奇迹集》《发现集》等。译有《卡瓦菲斯诗集》《巴列霍诗选》、苏珊·桑塔格《论摄影》、布罗茨基《小于一》《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火:鲁米抒情诗》《希尼三十年文选》、希尼《开垦地:诗选》《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等。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年获单向街·文学奖首届“年度致敬”奖。
主理人:方雨辰执行编辑:KD
进书友群请加小雅ya
点击看到更多好书
欢迎转发分享~
推荐阅读
弗罗斯特
我曾是一个熟悉黑夜的人(杨铁军译)
卡埃罗
如果我年轻时死去(程一身译)
露易丝·格丽克
感官的世界(柳向阳译)
我就知道你“在看”↓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gdnyy.com/wazz/1232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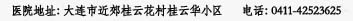
>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