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艺术家middot名家展台晏
诗人艺术家小传:晏榕,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重要代表及理论家,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国际诗歌交流与研究中心主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严肃的独立写作,作品千余首,其中长诗30余首,代表作有《欢宴:晏榕诗选-》、《抽屉诗稿》、《悬挂起来的风景》()、《汉字》(首)、《东风破》(首)等,另出版有诗学专著《诗的复活:诗意现实的现代构成与新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谁在说话:论现代诗歌文本中的主体角色》(即版),并有译著多部问世,被称为“为中国当代诗歌赢得了尊严的诗人”。
晏榕90年代代表作之《儿童画》
选自《欢宴:晏榕诗选-》
1
深夜,雨落自一幅儿童画,上面的春天
也变得潮湿了。屋里不再显得漆黑。
倒是台灯的光线更显苍白,腥松无力地
闪动着,虚弱得
像患了一场哮喘。而且
它那么固执,一秒钟一秒钟
挪动着,漫延开来。
以此方式
它们进入梦乡。这些童话融化成了水滴。
而季节实际上是在偷偷转换着。
所以,我猜得出
它们低沉冷漠的脸色
一定与连日来的天气无关,
也与几十年的生活无关。
我知道水滴也可以再结成冰,
一切沉睡的也可能再醒来。
寒气袭人。
我久久凝视着这幅画,体温保持不变。
屋内的摆设构成了另一幅画,一动不动。
还有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更远处的
黑暗,墙壁,屋子以外,还有
那些风,姿态和声音(而水不断滴落下来),
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我的位置。
但它们呼吸着,胸脯起伏得
那么有节奏,我
不只一次惊讶不已,那些笑靥的痕迹
虽然短暂,可毕竟是真相,我以为。
2
也可能完全失踪。
这一切
不是来得太快,就是太慢,
让人将信将疑。
不可能
总是站在一个位置
就把什么都看透了。
雨是淅淅沥沥的,可以用虚实相交的直线
画出来,或者干脆不画,这是
最好的白描。
其中有我的家人(按我的理解),
目光依然慈爱、严厉,从过去到未来。
我能从中看到许多,有些
甚至尚未发生。有些要在下一代人中发生。
但我必须将此铭记,必须
用同样的方式,本质上相同,
完全相同,而不是遗忘。
那么
所有的人就都是幸运的了,
我自己也在里面。
3
我自己也在里面。
那年我六岁,刚学会想象,但还不能
把一切看成平面,看成游戏之作。
现在想起来,在那时
它们就已存在,而不是后来偷偷溜进来的。
4
这些水一样的黑暗,可以从最小的缝隙里
渗进来,不占据任何空间。这是
最让人担心的。
春寒料峭之夜。安居之所。
有些事物在缝隙外偷窥,
有些事物已“长大成人”,不再将此当作秘密。
我始终要将其藏于身后。
不过,它们也许会视而不见,真的,
我真的希望是这样。
5
而且,还有风来自这个年代或者
上个年代的某些角落,
风卷残云,使记忆模糊。时间就会
彳亍不前,身体晃动,不辨方向。
一日长于百年。
我相信我俩的想法是一致的。
仅仅是年代相隔,这并不重要,我还在
欣赏它,像约了老朋友。
就像这下了无数次的雨
其实只是一场雨。这无数个春天
其实只是一个春天。灯光也一样,无边的黑暗也一样,
恶行与美德也一样。
但它们
还是保持着睡着的模样,蜷缩在
庙堂之下,或者,仅仅是
为掩藏这满目的情欲,叶片翻转在童话世界的
一个黯淡下来的影子。
有很多事
我们不得不报以宽容之心,
把它挂在墙上,忍受思念之痛。
把它放到弯曲的时间里,聆听
永不静止的水声。这秘密
只有你俩知道。
6
我肯定不会明白,尽管那时候我曾以异样眼神
将这些什物一一打量。两种不一样的
麻木,可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多糟的事。整整二十年,一个时代,
可以一遍遍地揣摸、解释,可以放纵到
海枯石烂。
可你在哪儿?那撩人的征兆都被遗失在哪儿?
而春色满园,时节尖锐地叫着。
冥语如花。那气味已消失殆尽。
再也回不去了。
7
于是,我试图用另一种仪式
将它代替。我听见它们说
这是一厢情愿。
但没有其它办法了。
仅仅
耍个小阴谋,把它
看成另一幅,一个摇晃着的世界。
但同样不需要
讲究表面形式,那逝去的部分
也许更重要,它们始终沉默,
藏在那儿,丝毫不理会新绿的挑逗。
始终睡着,冰冻如一场无可奈何的
婚姻。而那露出的部分
竟如此滑润,八面玲珑,可以重复利用。
可以一遍遍地死去,感动长者和少年。
无可挽回。
这就是它的迷人之处。
我可真聪明。
把它看成另一幅。态度诚恳
认真。
察颜观色。
这充满了危险。
8
春天仍在延续。
灰色屋檐下的梦魇仍在悄悄滑行,从此生
到下世,带着变化多端的羞涩欲念。
它如此让你难以割舍,直到小小的奇迹倏然出现。
(年3月26日-27日)
晏榕年后代表作之《忏悔日的书笺》
(选自《欢宴:晏榕诗选-》)
1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陷入了
一阵眩晕的惊慌,黑暗的风阵阵袭来
让这平凡的日子躲闪不及。我伶仃的影子
如一片树叶,可能在任何一个瞬间被风卷走
这些诺言仍高高挂在那儿,让房间里的什物
担惊受怕。我看到书页被翻开,飞虫儿
诱惑着曾经牢不可破的意志。多么地危险
我与这片刻安宁擦肩而过,没有预警
没有帏幕的摭拦,炙手可热的记忆
像欲望一样降临,毫无羞耻感可言。
2
一切都被虚构着,一切都被制造着
如一个女人走路的姿势。这湿润的习俗
已被凉晒多年。在这不动声色的
长久睡眠中,它无辜的热情正被悄然冻结
剩下的是宽容,是无边无沿的
液态的虔诚,就像这挥之不去的
发霉的天气。而且事物们一遍遍地
单调地惊喜着黎明,似乎唯有如此
方显出它们的固执和黑夜的虚弱
现在想来这一切是多么地不可原谅。
3
一个人独处,镜子里若有若无的脸孔
不止一次地冲着你微笑,让时间燥热难奈
用什么来代替这个不幸的词儿,这春暖花开
的一瞬,使一切个体都披上了耀目的白色
它的独裁甚至戕害了最犹疑的信仰
我一个人独处,变得冷酷而狡猾
成为一种中性的存在,像这空气,或者
书架上的陶女的轻挑的媚眼。然而
那脸孔依旧红润无比,俨然是个胜利者
我不敢轻举妄动,甚至不敢下定决心。
4
投诚或者反抗,自我孩提时代就萌发的
纯洁念头,现在又一次装饰于黑夜
面对它的诘难,我从容自若,对答如流
粉碎着一次次小巧的阴谋。这恐怖的灵感
曾经无所不在,藏身于我们看见或看不见的
事物背后。这是纠纷重重的一刻,梦中的阳光
显得苍白无力,拒绝任何一张嘴的比喻
显然在此之前,某个事件已悄然诞生
许多声音合为一种声音,用不着再加以分析
但上帝仍在远处伫立,保持着永恒的缄默。
5
这是个假象,我看不清楚它正在消隐的轮廓
谁在路上,谁已疲倦,谁会毁灭
在它们中最终会出现那个迷路者
披金戴银,以时间的气味断明方向
它那么纤细脆弱,我无能为力
无以表达,不论通过陈述还是臆想
就像窗帷挂在那儿,随房间里的风
微微颤动,你可以说它存在着,也可以
认为那花纹毫无意义,是个虚设的圈套
但每个面对它的人却总显得出奇地乖戾。
6
如何来相信,纯粹的火焰已被想象玷污
我奉承了那么多好话,它现在却像个
久病的患者,眼神呆滞死灰一如连日来的
天气。我是认真的,这图画已被我
描摹三遍,我还准备为它镶上边框
为它配上一束花,紫罗兰或者丁香
第一个事件和第二个事件形式迥异,却共同
承载了我的焦虑,这有关生或者死的
严肃问题。这黝黑而漫长的静寂,这隐情
已让我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
7
这之后,那声音再次提醒我,腐朽的气息
将漫溢整个季节,传染上瘟疫的亡灵
将拾级而上,把垂直的影子竖成八月的旗帜
信念会在风中曛黑,儿童们不再拥有
暗蓝色的记忆。而叠加起来的日子们已被
宠坏,没有秩序地嚷嚷着,耍着性子,像这纸上
不辨是非的黑体文字。这过程中
谁被伤害谁伪造了不朽的奇迹。啊,这原因
从未有人讲述和揣测过,从未有人
突发奇想,做出那个小心翼翼的假设。
8
作为报答,我把尘封已久的诗句统统抚摸一遍
让我惊讶的是那些秘密居然完好无损,它们
依然遵守着当初的许诺,连颜色也没有变更
那嘀答声依旧断断续续,深不可测
透明的幻象暴露无遗,风干在爱与死的花园
她的性情依旧腼腆可人,如我门外
饥肠漉漉的植物。我该怎样隐瞒该怎样
把这细小的颤音像孩子一般拍睡
我该怎样解释怎样遗忘,让长大了的现实
毫不介意我的双重身份,这对我是多么地重要。
9
然而我病得如此厉害,我不能容忍
有些事情再次复生.它们紧靠着我
挤压着我,既不睡去也不醒来
这景象一定壮观无比,如蓄意良久的
一次爱情,短暂而热烈
而我不想成为勃拉姆斯的牺牲品
我宁愿保持这模糊的听觉,靠一场雷雨
赐予的免疫力,遗忘着白昼连绵的戕害
我没想到这隐秘的仇恨竟会如此完美
真的,它的节奏微弱而欢快,动摇了我的决心。
10
但我无法看见这一切,哪怕只有一次
分离,哪怕所有的白色都自视野脱落
哪怕时间也变得老了,我之存在成为冰凉的
墙壁或洞穴,也不会博得她的欢心
我用了所有的激情,所有的盐、墨水和阴暗
来捕捉她的完美,来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但我无法辨认,这诗的最细微的元素,从一个角落
移到另一个角落,躲避着词语的驱赶
这意志力的流亡者,她是个用错的词儿,休止符
她只是个身影,出现在我神思迟钝的一瞬。
11
这是块巨大的帷幕,可以吸纳复杂或
不复杂的危险。它静静挂着,作为夜的依靠
宽恕着一首诗的诞生。没有一个细节可以
被忽略,即使时间已变得如此紊乱多疑
没有诀窍,没有臂弯的庇护,呼吸
也是居心叵测的,侵扰着漆黑的梦魇
而我恰好匆匆赶到,使这残损的映象
装饰于失语的黎明。越来越清晰
那纯洁的花儿正在打盹儿,一声不吭地
倦缩在帘布的一角,这痛苦已不能复述。
12
我已毫无戒心,面对这绿油油的幻象
女人、书籍,以及酷热的月份
它们比我还要羞涩,偷偷然而一刻不停地
注视着那个漏洞。它越来越大,像要把
所有黑黑的念头吞噬。眩晕感反反复复地
来临,如此猛烈、细腻,一次次
冲毁了意义的堤防,忐忑的午后
而离别的方式,问题的核心仍显模糊
这幸福,这无可弥补的运气一丝丝
脱落在地,像我久未梳理的长发。
13
我宁愿受此奴役,偶然性一触即溃
必须承认,这些在星期天堕落的事物
让我兴奋不已,手指紧张而痛苦
这只是个预感,在词语的内部发生
现在却蔓延到整个雨季,惊心动魄
没有秩序的美,慢性病,我为此
欢呼或惴惴不安,冥冥中推门而入
只剩下金属的敲击声,硝烟神奇地散去
捉摸不透的事实更被另一个事实隐藏
我宁愿独饮寂寞,受着它漫不经心的戏弄。
(年8月)
抽屉诗稿(50选5)
??之一谶语与狂欢
从一开始,这道光线就挂在那儿。
死亡。比文字间的缝隙还要狭窄,比白纸还要菲薄。
所以人们往往视而不见。作为生者,他们像石头一样径直奔跑过去,一天一天地纷纷落进去。可永远走不出光线的另一侧。
而鸟鸣就在另一侧,甚至连一声鸟鸣也走不出。那是挽歌。
我忽然想到,上帝会感到悲痛吗?他制造出了这面镜子,哦,双面镜。
一天一天,一路言笑。扭曲的身影犹如纸上舞蹈的文字。时间永远是遥远的,不论它指向前还是后,左还是右。
它像窗外叶片一般招摇。幻象复制着幻象。谎言连缀着谎言。谁能穿透它?
看,连枷锁也是遥远的,连喘息也是遥远的。所以,只剩下了喜剧。
世界乐在其中,一步步,朝向那水银的终点。光明的黑暗。意义。无意义。但在这里却被分开了。
那些躯壳儿匆匆而过,表征身份的服饰、衣帽、高贵的什物、奴卑的骨头、王者的口气……当世界全都落入那道光中,大地会在什么地方?
它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并以此构成了莫大的喜悦。
这真是些贵重物品。而我只有将躯壳打碎,才能成为观看者。
灾难。更大的灾难。欢声雷动的灾难。却无法让我与受难者和解。
打开房门,向外走出十步,再退回来。这样来拒绝,以灵魂的名义。而不是充当一个鼓掌的人。
听听,每个角落,每个片断,都在鼓掌,都在唱和。时间,唯一的绳索,被拉成了盟友。
所以必须彻底拒绝,用肉体。呼吸。用每一根竖起的汗毛和抽搐的神经。让所有的事实成为一个事实。
当血淋淋的夜幕降临,它就会把一切命名为黑色,万物似乎由此言归于好。
暖如春宵。一刻千金。
这由经验带来的无知,隐藏在我们光润的皮肤下,但我们却赖以生存。
没有心悸,不需要沉重话题。没有邪恶,不需要连连惊叫。
而春天里的末日就像染上了性病。脸蛋儿白里透红,香味儿四外弥漫,舌头幽居独处,牙齿密不透风。
因此所有的拒绝也只能是一种拒绝。水银之外,文字的呼吸,几乎成为一种怜悯。
而当咖啡里加入了菊苣,界线终于消失。
有名无实的生存,恰如一只圆圆挺腹的水果。没有核儿。也没有刀子。只能靠粗暴的想像来维持其枝头的摇曳。
一样的阳光和雨露,一样的疾病和不安。新道德。这成了秘而不宣的法则。一个时代的奇迹。
瞧,我们的世界都是机动的,马达隆隆,什么也不缺。
界线处处消失。
被粉碎的可以改头换面。被珍藏的可以丧失殆尽。独立可以妥协。利刃可以磨钝。姿态可以扭曲。少年可以老朽。
可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可理喻的和不可理喻的。可证伪的和不可证伪的。可憧憬的和无可留恋的。
流亡的和定居的。裸露的和掩盖的。疯狂的和正常的。腐烂的和勃发的。
浪漫与伪饰。假意与真情。生者和死者。石头和灵魂。
思想。另一个思想。形式。另一种形式。
于是“大众”再次出现。涛声。更多的大众。像鱼群一样沉浸在光明深处的丑陋里。
连夜里的呻吟也毫无二致。生活,呵呵,既等同于欲望,也等同于思想。
四月的馨香漫延成了白色的海,淹没了春天的尸骨。
孩子们。稿纸。雪中道路。银铃的笑声。在心中生长的少女的树。甚至谜。存在之物和不存在之物。也溺死了。
接下来是午睡的谎言。所以月儿高挂。仿像。
但仿像抛弃仿像。恰如一座城市的地图,挂在大小街口的地摊儿上,没有摹本。这才是真正的作品。
只需一个眼神儿,就瞥见每日来临的风暴。
这颓废的白纸,堕落的词,发麻的手脚,体内的小小王朝,绝不再是我一个人的危机。
呵呵,彼此都是一天,彼此都是观众和演员,彼此都是现实。超现实。
用谎言来谴责也能让它哭出声来!
果实开始无限膨胀,模糊了所有时节的轮廓。毁灭。在仪式的宫殿中。毁灭即宫殿。
黑白交配的时刻,鱼的影子们也燃烧起来,炫耀着各自的姿势。
陷落。大地之所。这是词语唯一的方式。在冷酷游戏中享受面具下的幸福。
花朵终于绽开,那是词语和它的服饰。它的家族。它真正的魅力在于挑逗了阳光,也撩拨了黑夜。
之后枯萎,弃绝整个花园,和充满淫意的春天。而时钟必须是静止的。
海必须是静止的才能迎接一个婴儿的诞生。
那道光线依然隐秘,露出一丝得意。一个寂灭的终点,映照着躯壳儿们弯曲的倒影。
他们幸福奔跑的姿势就像花瓣儿的颤抖。另一种死亡。
那是只双面镜,两种时间。崩溃的和悄然发育的。两种生者。死亡之下的,和死亡之上的。
而狂欢持续进行着,场面盛大,大家真的都在笑。
酷似初夜的节庆,以无目的为目的。
只有词语被击溃在墙角,保持诙谐口吻,互相插科打诨,既不是启发,也不是拯救。
只有它们,眼睛沾湿,看见了一切。
??之二伪装之域
黑暗。小巧的容器。却能容下所有的人,所有麦粒儿般的名字和它们的叫喊。
所有的风,坚硬岩石,摇摆的姿势。时间缓缓倒下的样子。
那些经历过冬天的树桠,已学会装点死亡,怀念或者遗忘。把美诞生在恐惧里。
所有的液体也在其中,酒,幽秘的梦,没有归属的鲜血。所有的大海。渗入日渐萎缩的边界(那只是个小小的括弧),僵硬的地缝儿。
只有灰烬在发笑。从未安息的兄弟们,你们可曾忆起你们来自四面八方的风?
来自燃烧的阳光和跳跃的波涛。巨大的手。花蕾。肉色的水果。
而今你们加入了阴影的队列,阴影重叠着阴影,像凝固的旗帜。笑容也凝固了,带着被俘者的幻灭。
而我像个隐居的人,安顿于危险和救赎之间。在这细细管道的两端往返不停。从耳朵到嘴巴,从眼睛到内心。
从高耸的纪念碑到被掘出的骨骸。
两种颜色,都在昏沉沉的睡眠,它们认为这是值得信赖的补偿方式。
所以,美仍在繁衍它的后代。恐惧感被互相复制,如此琐碎,夹杂着雨水和火焰,思考和斗争。
敌人,不光制造了锁链,而且走入了我们体内。敌人以我们的面目出现。
新技巧。包围和填充我们。隔绝和分解我们。最后,我们就成了敌人。
但它看起来就像是在挣扎,恰如时间是在一滴一滴地淌血,反射着没落帝国倏忽而逝的微光。
看,主人公们怀揣纸笔纷纷造反。改编。原创。不分昼夜。现实被压扁。超现实被拉长。
牙齿不再愤怒。金属穿上了睡袍。时钟们被告知:保持沉默。忍受。忍受。不光对死亡,也对沉默自身。
我发现,“我们”是有限的。连“我”也是有限的。
这是严酷时节的礼物。花朵不再居高临下,欣然与橱窗里的烟味儿契合,啜饮黑夜。
人声鼎沸,但街道消失了。涛声依旧,但大海倍加荒凉。
实际上,花蕾刚过子夜就开始嫉妒起黎明。昏睡的人对所有的呵欠表示愤怒。而这是我们尚未发黄的扉页。
软绵绵的近代史。
羞辱。不存在智者与愚者间的较量,只存在如何抵挡(转化)羞辱。小小的唇。咸腥的发泄口。
从夜至晨,书页被倒着翻了过去,回到一把冰凉的青铜刀子。
退化。我们称之为生活。当大海退去,还有什么是无边的呢?
呵呵,只是一间卧室,装饰一新(遥远的风暴挂在墙上),盛满了遍体鳞伤的裸睡者。
这是用来布置清晨的物品。石头。生锈的铁器。未干的衣服。发霉的长出绿苔的词语,和心脏。
最新的诗歌。浸着毒汁的报纸。扔进垃圾袋的避孕套。
用它们充当四时的祭物,避开厄运。
讨好视力低下的酋长,向他禀告寒冷已远,疾病痊愈。玩具已被抛弃。嘴巴全都张开。
那只泣血的飞鸟仍囚在它的笼里。长触须的虫子们在匍匐前行。
容器里充满了甜味儿。漂流的词语会一一返还。
只剩下一堆语言的尸体。赞美。一切都是贡物。这竟然成了辨认我们自身的依据。
全知。先知。一无所知。
我们是可恶的,还是可怜的?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
那在风中写作的人,只是为了把自己从身体里推开。
一片叶子。谄媚的舞女。像鸡肋一样的修辞。不是被自己推开,就是被自己占有。
一千个梦只有一个结局。一千个结局都在一个梦里。
花瓣碾入泥土,大雨倾盆而下,你还想还击吗?
于是,时间的伤口被舔得发痒,万物萌生。像呼吸一样可信。
退化也有它的秩序,宛若病毒,长着美丽的枝条。可以统治一个春天。
一场崩溃。批判的孑然挺立。反批判的落叶归根。
真正可怕的是(这可以看作是美的极致),它决定了所有骨头的命运,灵柩的方向。
一天,一年,一个时代。不会有奇异的话题。
有选择的必要吗?苏醒。逃避。向上。向下。小秘密。
其实,连这一时刻也是被指定的。
伪装之域。“一”的世界。
只有。一块土地,一座石碑,一张笑脸。一条道路,一家旅店,一套制服。一份报纸,一台电视,一个声音。一种天气,一个旋涡,一个时令。
只有。一部小说,一场戏剧,一个作者。一份宣言,一扇天窗,一束光芒。一个高度,一类思想,一款罪名。一种诞生。一种死亡。一张白纸。
但有一种伪装是不同的,以伪装对付伪装,带着诡秘的笑容和空寂的心。
狂喜。以沉默的方式。或者相反。在黑暗中寻找黑暗,聆听钟表内心的私语。
我始终相信,在暴露之前,它在悄悄记录着什么?
饥饿感。连它也是虚无的。
苍白蒙蔽苍白,边界消失。它只是个小小的括弧,却要来终止一切。
喘息。一只空空的碗。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生还。
??之三缓慢的时针
它变得越来越薄了,一个日渐瘦消的季节。小心翼翼的绽放和仪态安然的萎落。谋杀。
它正悄悄把暗红的印痕拖长,那些迷人的信仰,风干的血,和正在变得性感的阳光。
它把镜子收起时,也把每一件事物密封起来。石棺。弯弯的一秒钟。轻巧的一个pose。
一滴滴地蒸发,一寸寸地腐烂,别无它虑。
而影子纠缠着影子,披着光彩照人、霓裙罗裳的诸世纪。
是的,冗长的日落。正常智力。
墨绿色的文明,隐伏着野蛮的长矛、苗条的旌旗和相互调情的篝火。
尖锐的风划过两个身体,一个巨大,一个渺小。两个宇宙。海水和岛屿,遮蔽着漫无边际的冥想和孤苦伶仃的日子。
却都潜藏着呼号(有人喜欢说是呐喊,他们太容易相信并依赖嘴巴),高亢如日,微弱如星,沉寂如尘。
哪一个是我们的模样?可以让那把乐器弹奏出这阳春的本来面目,可以区分花朵的神气和我们从中领略到的哀伤?
哪一个正将绝望拖长,再拖长,等候着我们的辨认?
而熄灭的分明是四个世界:一个是感受的,一个是描述的,一个是本在的,一个是猜想的。
这可以看成是一场乱伦。洞穴与灯盏的博弈。
哦,还有一个伟大的书写者,圆睁双眼,目不转睛,直到它们全都被封入容器。
冷漠的陶土,热情的梦想,单纯的水晶,神秘的铜。
透明的幸福。不透明的痛苦。
当这些钟点全都深陷入时间的污泥里,他的笔端正好吐出月亮,鸟儿正穿越黑色。
但事实上恰恰有一个世界溜了。物质。反物质。永远的错误。而眼神就是那层迷雾。
只有带腥味儿的身影在相互拍打,以石块和浪花作为应答。
它像个老者,佝偻着身子,似乎还患了肺炎。昼与夜,潮闷如一声冷笑,咳嗽。折皱的纸。
我猜想,是我们的任性使它放缓了脚步。
大地之上(我可以说“尽头”吗),白色的思想波涛一样堆起,雾霭一样喜形于色。
而那里已没有了暗语。诗歌的把戏。和那流动着的被称为知识的岩浆。
花朵也熄灭了,昆虫们收起了触角和蜇针,没有什么会溶化眼睛,也没有什么能刺疼皮肤。
只是延续,从延续到延续,那些“主义”滚动得像砂粒一样好看。
真的,鬼鬼祟祟是个漂亮的词儿,既可以描摹心理,也可以计算脚步。
这使我想到海德格尔,呵呵,三种烦。但只能活着,不得不活,全都是活。
你可以说这是剩下的王国。遗迹。就像我们遭受掠夺的身体。
就像熵。缩小到黄昏七八点钟。小小的胃。消化了荆棘的混乱和刺猬的雄心。
集体无尖锐。
所以蝙蝠出动,让小新闻们在空中爆炸,超声波的世界里,不需要哨音和交谈。连渐渐褪色的拍翅、翻滚和重叠也是多余的。
暗灰色的斑点,娱乐天地。飞翔。
其实,只要它停在那儿就行了,只要它是冻着的就行了。对,那小小的海,那时针指向的——寒冷。
只要屏住呼吸就行了。假象的艺术。以现实的形式。
奴仆们偷偷藏起石头,堆砌在通往星期天的路口。它们坚硬得多像我抛弃的诗句。
而心如磐石——这似乎还远远不够,那就再加上——火如枯血风如铅。每一个想法都成为我冻伤的脚趾。
少了点儿疼,多了些痒。这是合情合理的赔偿方案。
谋杀。不动声色。以丧失的方式赢得自身,真高明。
那就消耗吧,并使生活合法化,一遍遍地消耗,一遍遍地生活。
让这群孩子像虫卵一样蜷缩在静止的一秒钟里(过于寂静的时间还是否属于时间),并且,害怕一个想法远甚于一个事实。
真正的监狱。关于毒汁的一则小广告。不光是季节生病了。
我隐约觉得,帏幕刚刚被拉开,而不是落下。
当白天背叛白天,黑夜侵犯黑夜,那动弹不得的究竟是什么?牙齿,舌头,还是整个时代?
一出好戏。关于一丝光线,关于那声不和谐的鸟鸣,关于沉没。
白日梦,闪电的国度,颓废的手指,生活笔记,装聋作哑的智慧,还有死亡的日期,都只能作为装点。
真正的核心只是一个谜:人。
醉醺醺的房子。窗前有窗,门后有门。这只是一场风暴的内部。一个蕊和它害羞的梦。小岛屿。
可它会来吗?它在吗?它正和“时间”这个词儿挤眉弄眼。噢,戈多!戈多!
花香弥漫。蛹在嗥叫。两幕风格迥异的独白,居然能同时上演,美的分娩。
词语在筑巢,黄蜂在挑衅春天,新绿在焚烧,煤在撒谎,高高竖起的头骨在寻求敬意,而花岗岩已经溶化。
被串起的宝石。这些是还没被分光的财产,可以寄存在地平线上的那抹黝黑里。
兀鹰守卫着夜。笔依偎着白纸。缓慢搏动,微弱到像茕茕孑立的纪念碑。
关于它们睡眠或者醒来的传说,我只能略述如上。新世界。
而且据称全都装了进去,自然的和历史的,貌似从眼睛到心灵的距离。
??之四暗如星子的人
人啊,暗如星子的人,沉睡在黑白交汇的微光里。两个世界的嗤笑,恰如催眠的新式牧歌,排泄着花朵的污秽。
那么情意绵绵又危险的交锋,划出了涟漪般的伤口,曲折诱人。淌血的闪电向远处不断推开,成为硕大空洞的眼。
一个刚刚发芽的暧昧景致。
这就是界限,大大小小的城池,圈定了那么多五光十色的轮回。
而在地垅的边上,斐德若又在问:“你从未出过城门吗?”我不知如何作答。干脆,把它理解成一个身体的问题。
正如这些文字和它们的阴影,谁是谁的符号?谁在驱赶谁?皮肤隐瞒了一切。
但那陈列其中的似是而非的微笑,像闪耀的残缺的月亮——盛着我们的归宿。
乱草丛生。经验的人,聪明如蝙蝠的人,吐着白色呼喊的人。
吟诗的人,口袋里装着自己的轻佻身影和孩子般被宠坏的黎明的人,在腥腥的三月闭目打鼾的人。
骄傲如一道弯弯的睫毛。时间的新装扮。
而饥饿的幽灵们纷纷出动,拖着压扁的名声、遗言、床垫儿。小坟茔。
他们都在说,那节奏、那震颤就是他自己的呼吸,那大地的波动,就是他们在和自己舌战。
这是第一个条件,可以凭此摸寻到那些瘦削、扭曲的脸。
这是铜镜。反向的黑暗。照得见那石头的怀念、花蕊的哭泣、大树内心的摇摆,还有掩埋时间尸骨的傲慢。
照得见被剥开的春天里,那些黄铜飞翔的姿势。
弹痕累累。
十年就此倒下,蜷缩成一天,一个黎明,一次逃亡。二十年就此沉睡,蜕化为粮食,村庄和空空宫殿。
而野兽成群,出没于模糊不明的路灯下,进行着羊皮的交易。
既说“不”,又说“是”。
连最细小的想法也被瓜分了。完全的对称。一丝不安紧跟着一份得意,一阵隐痛紧跟着一片欢呼。这是第一个宗教。
但我不是悲观论者,也不是怀疑论者。就像一只圆圆鼓腹的水果,或者它静谧的核儿。
沉睡也好,做梦也好,还有那些花枝招展的形式,屈指计算的运气,甜和苦,热情和冷酷,有什么不妥吗?
至少看起来,它们都还像是可供欣赏的对象。坠落可以流转起舞,腐朽可以挂着笑脸。
有什么不妥吗?它们早已不是那个春天的副本,它们是自己的副本。
于是,在某个寒冷时刻,这些被移植的躯干不得不以想像为食,靠着词语取暖。拥抱。亲吻。身体的扭动。意志的喘息。
爱在打圈圈。
搭配上文化衫的汗渍,符号里的脸,星星睡意惺忪的眼神,原野上孤狼的声声嚎叫。
呵,那荒芜之夜,我们竟不能将之扩展到一个年代,一个洞穴,或但丁在黑森森前的一次眩晕,蒙田在冰冻的葡萄架下的一次战栗?
这算不算患上了失语症?
于是活着或死去的问题不再严肃。这似乎不是件多好的事儿,可也坏不到哪儿去。
你看,那么多人活动着四肢,粗壮的,纤弱的,就以为触摸到了时间。
(实际上,那只是一张打着粉底的脸,和永恒无关)
而同时,那么多时间的肢体被我们冷冻了。当血液不再流动,还会有思想吗?
其实,应当这样问,当思想成为一堆固态物,活着抑或死去还有意义吗?
手和脚,嘴巴,身体。姓和名,口吻,家世。爱和情,背叛,遗忘。你和我,日子,生活。不幸之大幸,毫发无伤。
而那个最初的用来辨认自己的念头,显然可以归于命运之误会,我们甚至可以讨巧地说一声——那是场灾难!
就当我们被切开了。支离破碎。血迹斑斑。
一半瞒哄着另一半。而且绝不会一劳永逸,对,一半的一半,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而它们曾经盛满诗歌,盛满空无一人的大街,或作为一枚奇异的水果拼贴在街口的招牌上。
现在它们各自互不相认,互相嘲笑,激愤地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对方。直到心甘情愿地用对方的名字称呼自己。
呵呵,切开的人,须用尘土变回他自身。
魔术。一次冒险,许多次冒险,集体的冒险。变幻莫测。
大地用黎明和黑暗来冒险,我们用肉体和灵魂来冒险。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共同完成那镶着金边儿的荒诞,而用不着半句辩护。
那穿透和扭曲的神力,并非来自天宇,而是隐藏起来的“另一半”。
我们都有罪,连那些空空的摇椅也是有罪的,连门把手也是有罪的。
新道德。光彩夺目。哦,奇妙的磁石!哦,哈哈镜!
我们是这世界的任性的孩子,和这世界是我们的任性的孩子,是一样的。这是荒诞内核里最美丽的成份。
这时描述西绪弗斯的故事是难为情的。最好收拢触角。最好一动不动。
走出城门,意味着灵魂出窍。
在壁橱的硝烟里,依稀可见精装书们疲惫的神态,它们鼻青脸肿,阵脚大乱,刚刚经历了肉搏。
有些在胸前炫耀着战利品——遥不可及的“高尚”、快如闪电的“爱情”、包裹严实的“伦理”、笑容诡异的“运气”……
还有几个掂着脚,怯怯叫着——“这和我们无关!我们是复制品!”
结局如蜷缩的草。
噢,不。结局如夹在书里的三叶草,发霉了。
孩子们在花园奔跑。矛在地下。梦。血河。迟疑的大雾。这不是我们的身躯。
90年代代表作之《幻象与时光》
选自《欢宴:晏榕诗选-》
幻象与时光
1
在黑暗的
文字缝隙里
有一束形而上的
闪电
使我的瞳孔
张开
使钟点失眠
你的名字像雨点一样
落入黑夜
梦的泉水
喷涌而出
浸湿了石子们的想象
梦游者
从黎明的影子里走出
道路消失
寂静开始生长
像海一样扩展
像火一样疯狂
2
你来自
四面八方的风
来自黑暗自身的血液
(报复啊!报复啊!
视野里的树木
正无声无息地燃烧)
天空旋转着
你来自唯一的一片叶子
把树木的语言统治
和它一块儿
燃烧,成为
火光闪动的一部分
而我好像听见了
体内水滴的呻吟
以最温柔的一种语调
3
一块没有光泽的金属
一块形式的骨头
在那儿收集寂静
那隐忍的力
来自尘土
空气和水
来自你清晰可见的影子
我能听到
它们躲在事物的内部
流淌,像美妙的歌声
(请抚摸一下
请亲吻一下它白晰的肉体吧
让词语的光辉
照亮它最隐秘的想法)
一次宁静的
呼吸后
我似乎沉入了最深邃的幻海
4
这模模糊糊的
一切
我所能想像的
只是一个饥饿的
黎明
那些光线
微弱而柔软的触角
伸入我微痛的伤口
一只又一只
巨大的张开的手
从我眼前晃走
我觉得那就是
女人们赤裸的命运
在慢慢滴落
5
那是月亮里的血液
燃烧了一个晚上
寒冷的火焰
让人晕眩的
舌尖
我和那么多幽灵
擦肩而过
在黎明的门口
它们摇曳成一张张叶片
把你的裸体偷窥
它们呼吸急促
眼神胆怯而可爱
蓝色的植物们
在潮湿的空气里
自言自语
而且
在最静默的一刻
相互拥抱在一起
6
你尊贵的名字就这样
被灼伤
黑黑的血
流动在时间的堤防下
这一刻
没有语言的闪光
一个个阴影
却被淹没在记忆的空白里
(一种声音在叫
吻着我吧,吻着我吧
垂下你的秀发
让它们
像水草一样将我覆盖)
我看见乳白色的石头
在河中央来回摆动
从一个钟点
到另一个钟点
7
让记忆
像光明一样躲藏在
叶片后
这些
阴暗
潮湿的东西
会浸透
整个黎明
让坚硬的词语
叩敲你没有感觉的
胸脯
在赤裸的水中
游弋
你不要顺流而下
你不要
沉睡在两块石头中间
8
我听见了
它们贪婪的喘息
那些无边的黑暗后面的
野风
裹着警觉的雨水
将把我所有的想法
吞噬
只留下一干二净的
原初的大地和天空
之后
另一个绚烂的梦幻
会像星辰一般升起
闪烁着更为寒冷孤独
然而智慧的光
9
只有一个单词
在黑夜流浪
在水里漂泊
它的肢体
明晰又朦胧
古怪而优美
只有一把刀子
(它切断了你优柔的目光)
闪着痴情的火焰
将我明灭的意志划出一通长长的
伤口
那么迷人的黑色液体
那么迷人的眼泪
10
你如一个弃婴
陶醉于
不同寻常的命运
你如一滴
没有光彩的水
纯粹、自由、无语
你是一个沉思者
把所有记忆
驱逐在光和影的海洋里
一片悄无声息的海
静静地淹没着风景
汇入我充血的眼眸
不过
也许你只是
我一瞬间的灵感
注定要在短暂的白昼里销熔
11
但我只是一个
梦游者
被太阳藐视
被风儿撩拨
被黑暗遗忘
我终日被围困在
幻觉的墙壁
不能感受
花儿的温柔
火焰的温度
我的天空那么狭小
高傲、阴冷
使人目眩
只有戏谑的哨音
在一滴幸存的蓝色里延续
12
一束静止的光线
使这些泥塑
感到战栗
那些曾被闪电烧毁
又埋没于黑暗的事物
我垂下
红肿的眼帘
把一道道思想的铁门关闭
让一个个上升的
白昼
凝固在形式的阴影里
这时你的手指
像食人草一样伸开
攫住了它们抽象的头颅
那些不可理喻的
怪念头
13
这些文字
汇成了一条无湄之河
那么多憔悴的形象
泅渡其间
那些
像星点一样的文字
把孤独而幸运的岛屿
围拢
(它的喘息声一圈圈散开
使我着迷)
波光
鳞鳞
沉思的时间
安静地排列在
河的腹部
享受着被监禁的快乐
14
一阵突如其来的风
一阵眩晕
我感到
饥肠漉漉
像走进另一个空间的
陌生人
叩敲着锈迹斑斑的
黑暗的门环
神秘的鸟儿
雀跃着
传递出藏匿已久的伤感
我的嘴巴
大大地张开
吐出了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15
在最寂静的时刻
谎言一片片
坠落
像漂在水面上的花朵
你的倩影
也淹没其中
(谁来把它们点燃
谁在愤怒谁在高歌
谁来与我相识)
我看见一些
没有名字的植物
在冰封的土层下默默生长
它们的躯干
缠绕在一起
交换着各自的欲望
这时连晨曦
也悄然藏隐
一如语言的石块
窒息在我的喉咙
16
你就是我渴慕已久的
造物主么
而我是一樽
被岁月遗忘殆尽的
残破的石雕
庸俗的空气
凝滞的敬意
已在我身上划下那么多
暗灰色的细小的刀痕
我知道只有你的沉默
能把时光的影子
淹没
能融化这个黎明
最寒冷的意志
17
只是在微细的一瞬间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那绵亘又隐约的
足音:
“这是一条
没有尽头的河
永远
不能汇入大海
但是一切
形成自我的每个部分
每一滴水
都是永恒的”
我对这些
一无所知
于是只好
信以为真
并由此走向那遥远的出发地
18
这也许是我
全部的才智
都包涵在
黎明的一声哈欠里
这是最合适的
一个玩笑
那些光亮
原来
出自禁锢了我所有的想法的
一块金属
真正的太阳
就要升起
万物
(包括这些诡异的文字
看,它们把光明掩饰得多么神秘)
都将脱下它们
华而不实的外衣
19
闪耀啊闪耀
从存在到存在
每个发光之物
都设法在阴险的白昼里躲藏
(我什么
也看不见啊!
而你却要我用一生来相信)
这流动的水
神秘的光辉
我们的想象力
以及咒语
就这样迷失在一片苍白中
你的歌声在叶片间
摇荡着
然后穿过了黑黑的树林
20
它们都在谛听
那风中的一片
私语
一切都是透明的
包括
每个细微的过程
从生到死
从开花到结果
一切都会
燃烧起来
然后成为灰烬
一切都会被光线唤醒
从我的驿动的心
到你注视的眼睛
我知道所有梦的羽片
都会飘飞在你的世界
虽然现在
它们消失在白昼
就像冰山滑入了海洋
(年8月)
《诗人艺术家》编辑委员会
顾问:谢冕
主编:孙樱
副主编:楚子(著名诗人、书画家)
施玮(著名诗人、作家、画家)
周俊(著名诗人、作家、画家)
执行编辑:孙玲
孙樱
转载请注明:http://www.gdnyy.com/wadzz/1378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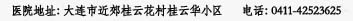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