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ngtaX塔吉克斯坦最好的帕米尔公
帕米尔公路似乎永无止境;我们的老式吉普和向导。
凌晨4点半,突如其来的地震把我从梦中惊醒,落地玻璃窗发出颤栗的咯吱声,在黑暗中尤其刺耳??没等摸到床头灯开关,一切倏又复归平静。我心有余悸地拉开窗帘,只见总统官邸的圆形金顶在射灯照耀下,仿佛刚降落的异星飞碟。
一些古怪念头闯入脑中:拉赫蒙总统是否也被地震惊醒?如果此刻他也正望向窗外,看到人工湖畔拔地而起的高楼广厦,一定会倍感自豪吧?
10多年前,杜尚别还是个彻夜宵禁、为内战所苦的困乏城市。如今,建筑物上的弹孔被抹平,西式现代建筑正将首都天际线上的苏联痕迹,逐一扫除。我住的凯悦酒店是杜尚别“新颜”中最流光溢彩的部分,从空中鸟瞰就像大写的英文字母“A”,令周围残留的沙丁鱼罐头般的苏联建筑,愈发相形见绌。
自由广场上的萨曼君主塑像;杜尚别街头。
“我知道一则轶闻,或许能帮你弄清杜尚别,乃至整个塔吉克斯坦发生的变化。”次日,好客的酒店经理Jan-Francois约我共进午餐:“拉赫蒙总统原本的姓是拉赫莫诺夫(Rahmonov)。5年前,他决定把斯拉夫语后缀‘-ov’去掉,就成了现在的‘拉赫蒙’(Rahmon)。”
说完,他脸上挂起法国人读《巴黎竞赛画报》时会有的那种微笑,接着话题一转:“尝尝焗烤龙虾,这在没有海岸线的塔吉克斯坦,可是绝对的奢侈。”
凯悦酒店是塔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五星级酒店。在此之前,一统天下的是老旧的苏联式招待所,贴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壁纸,由雄赳赳气昂昂的楼层女服务员“把守”——如果住客想洗澡,她们会慷慨地送来两壶热水!
用马赛克拼贴成的宣传画;曾经的丝路驿站希萨尔。
南北向的鲁达基路(以波斯诗人鲁达基命名)纵贯杜尚别,几乎所有值得一看的景点,都分布在这条城市动脉周围。我往国家古董博物馆信步走去,那儿收藏着年前贵霜王朝的睡佛、栗特人的湿壁画、大夏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象牙雕像,以及一柄六世纪的刀鞘——以神话里的怪兽狮鹫为造型。虽然陈列设施简陋,这座博物馆却是塔吉克人追寻血统和民族认同的神圣课堂。不时有老师带队的小学生团,把狭窄的参观过道堵得水泄不通。
博物馆管理员告诉我,现代塔吉克人的祖先可追溯到波斯萨曼帝国,塔吉克语属于西南波斯语系,与属于突厥语系的其他中亚国家的区别显而易见。我还从管理员那儿听到了另一则轶闻:年,萨曼帝国建立周年之际,自由广场上的列宁塑像被挪走,取而代之以萨曼君主IsmailSamani。他的形象也被印上百元大钞,以彰显其“塔吉克之父”的地位——强大富足的萨曼帝国定都布哈拉,撒马尔罕亦为重镇。
“都是斯大林的错,害我们失去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抛下这掷地有声的一句话,管理员转身去驱赶试图触摸湿壁画的顽皮学生。
想搭便车回家的学生;写在路旁山岩上的标语和涂鸦;马可·波罗羊的巨大双角;当地的健怡可乐。
走出博物馆没多远,一辆老旧的伏尔加汽车在我身旁停下,司机探头嚷道:“希萨尔?”那正好是我下个目的地,丝路古驿站之一,距杜尚别约23公里。出城途中,又多捎了两名乘客——在中亚旅行,合乘出租车既方便又经济。
出乎意料的,其中一人操着流利中文与我聊起了天。他叫法拉,公派在北京某大学深造,这阵子因病休学回家静养。沿途,他对自己祖国的变化谈兴甚浓,比如俄产伏尔加汽车正被韩国大宇淘汰、由中国援助修建的新公路、与乌兹别克斯坦龃龉不断的罗贡大坝——为解决长期困扰塔国的电力短缺问题。
“希萨尔是个怎样的地方?”我插了一句。
“没什么可看的,只有废墟。”法拉的回答听起来无精打采。
事实上,他也没说错。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只剩一道空门和两座朴素的经学院,还比不上印在20元钞票上的图案有吸引力。我爬上要塞背后长草萋萋的山坡,惊扰了几对恋人,登高远眺,试图用想象弥补目力的不足——毕竟,居鲁士、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帖木儿、阿拉伯人和苏联红军,都曾如飓风掠过希萨尔。
瓦罕山谷,河对面是阿富汗;牲畜和检查站是帕米尔公路的两大“路障”;一辆颜色惹眼的中国货车;跑长途的中国司机常光顾的路边小饭馆。
启程前往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的最后一刻,我拜访了IsmailiCntr。后来,即使是在与阿富汗仅一河之隔的边境牧羊人家中,只要我提起曾经去过那儿,便会受到主人分外热情的招待。这是因为它的创办人阿迦汗(AgaKhan)在整个帕米尔高原,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敬,家家户户都挂着他的照片。
在那儿做义工的Obid给我讲了一段历史。内战期间(年-年),自治州民不聊生,经济危机严重到人们拒绝使用纸币,只能以货易货。年,阿迦汗来访,创立慈善信托基金,拨款赈饥、修路搭桥,投入两亿美元在首府霍罗格建校办学,同时他号召人们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
杜尚别的IsmailiCntr是该机构在中亚的首站,免费向公众开放,发挥着文化交流和教育培训的作用。希拉里·克林顿就曾选择在此,推广美国政府资助的新丝路计划。除杜尚别外,还开设在伦敦、迪拜、里斯本、温哥华、多伦多,并剑指巴黎和洛杉矶。
而站在个人立场上,对Obid来说,正是阿迦汗的好心和善行,让他能在霍罗格完成基础教育后,前往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如今他是中亚大学的一名讲师,每逢周末便来做义工:“阿迦汗是真的圣人,你能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而非故纸堆里,感受他的存在。”
我们的向导是在塔吉克斯坦生活的吉尔吉斯人;超现实主义的双车道;已成废墟的丝路要塞;帕米尔高原之广大空旷,让山峦看上去就像土包。
“那片高原的名字是帕米尔,骑马要12天才能穿过。那里没有绿意、没有飞鸟,只有石头和沙砾。因此,旅人得带上所有必需品。如此空旷、如此寒冷,以致我不由得注意到,连火光也不那么明亮和温暖了??”
从杜尚别至霍罗格约公里,开车需要至少20个小时,路况之差可想而知。这倒也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重温《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帕米尔高原的精彩章节。这个勇敢的威尼斯人在年途经此地,留下的痕迹是用其名字命名的野羊——巨大的双角可长至两米,呈“S”型扭曲。
然而,有三个中国旅行者比马可·波罗更早行经帕米尔高原,即葱岭。他们是为争取大月氏联盟却无功而返的张骞,以及西行求法的佛教僧侣玄奘和法显。紧随在这些伟大行者之后的,是“大国游戏”中身份暧昧不明的杨赫斯本(英)与普尔热瓦尔斯基(俄)等人,既是探险家却也脱不了间谍的嫌疑,将世界上最奇异和遥远的山川,变成东西方第一次冷战的竞技场。
人与车都在风雪中摸索前进;帕米尔风格的石房子;一眼天然间歇泉;气温骤降,霜花在玻璃窗上蔓延开来。
就这样一路浮想联翩,我来到霍罗格。这个山谷小镇被两列几近垂直的峭壁,紧紧夹在中间,汹涌的贡特河穿城而过,直奔阿富汗边境。此地虽无甚景观,却是大名鼎鼎的帕米尔公路起点。
苏联的军事工程师们在年至年间,设计修建了这条高纬度公路,翻过海拔米的Ak-Baital隘口,途经千万年前因彗星撞击而成的黑湖(玄奘认为湖中有毒龙),一直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城市奥什。初衷是为方便军事运输,戍守“帝国”最边远的岗哨,直到近年才逐步解除对游客的限制。
在与向导Nurali仔细商量权衡后,我拟定了先前往瓦罕山谷,继而转回帕米尔公路并行至穆尔加布,最后翻越海拔米的Kulma隘口,走陆路返回中国的计划。
当雪山被第一束曙光点亮,我已奔波在蜿蜒崎岖的碎石路上,右侧是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界河——喷赤河,它也是孕育中亚文明的阿姆河源流。数不尽的冰峰高耸在前,绵延成排山倒海的气势。海拔米的兴都库什傲然其上,宛如皇冠上最大最亮的宝石,云朵为之匍伏,令人怯于仰视。
雪线以下,是草木稀薄的贫瘠石地,偶有牧人和羊群如雨后蘑菇突然冒出,衬得这片风景愈发壮丽而冷酷。新石器岩画、丝路要塞废墟、佛教和袄教遗址、伊斯兰圣人墓冢,隐匿于巨石之间、洞穴深处,得向导指点,才能找到门路。晚间,借宿在全用石头筑成的传统帕米尔民居,Nurali在倾泻的银河下吹起木笛,有那么一会儿,我竟恍惚不知来自何处、身在何地、去往何方。
好心为我们提供食宿的老妇人;清晨时分的边城穆尔加布;中国就在铁丝网后方;消融的霜雪恰似簇簇苔藓;越靠近中塔边境,路况渐好。
次日清晨,喝过暖身的热茶,继续上路。瓦罕山谷从后视镜里逐渐褪去,穿越海拔米的Khargush隘口转入帕米尔公路时,我出现了高原反应,偏又遭逢五月飞雪。原本春暖花开的天气,在10分钟内迅速降至冰点,继而涌起浓雾,片刻间就雪雹交加,能见度不超过两米。
在一片白茫茫中小心摸索了个把钟头,终于开上帕米尔公路,肆虐的雪暴也逐渐消停。待驶近穆尔加布,天空已是一洗如镜,蓝得令人发怵。
此地雪山环抱、地势平缓,是个吉尔吉斯人与塔吉克人混居的边城,向导的家就在这儿。Nurali告诉我,穆尔加布是帕米尔公路的中途站,由于毗邻全球最大的鸦片产地阿富汗,毒品交易一度猖獗,帕米尔公路也被戏谑作鸦片公路。
内战结束后,法国、德国、瑞士的非政府组织相继到来,以开展“生态旅游”的方式帮助当地人改变非法的经济格局。加盟的村镇通过向游客提供吉普车司机和向导,马匹租用、民宿、手工艺品等旅游服务创收。同时,非政府组织也发挥自身的国际背景和影响力,鼓励与引导旅游者更多“以当地社区为基础”的旅行方式,来探索帕米尔壮美的高地风光和民俗活动。
站在嵌着盘羊角的民宿屋顶,Nurali手指东北方,咧嘴一笑:“看,那闪闪发光的就是慕士塔格峰(位于中国新疆)。明天你就回家了!”
*塔吉克斯坦驻北京大使馆可受理因私旅游签证,无需邀请函。若要前往帕米尔高原,则需同时办理《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许可证》(GBAOPrmit)。
*中塔两国间唯一通行的陆路边境口岸为卡拉苏,距新疆喀什约公里,距穆尔加布约80公里。主要在夏季开放,塔方上午10点开始通关,中方则在下午3点,均为当地时间。
Copyright?-LungtaVoyags
李路lloo赞赏
人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gdnyy.com/ways/1048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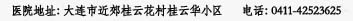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