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化文学外国诗歌教室奥登诗选和评论集
在《分水岭》的开头,风是“擦热的”(chafing),在这个场合之前,这个词似乎被剥夺了拟声的生命:现在,它允许我们通过它迟缓的元音和亲切的摩擦音来倾听风在山坡上的低语和摩擦。但是这段在呼吸上无法忍受的文字被一些摩擦物的意义弄得复杂了,被损坏、被磨伤而后红肿起来。这个词暗示留在身后的(分水岭的)地形学交接点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心理上的症结、一种遭遇两种矛盾状态(同时遇到一种彻底的寂静和一种沙沙做响的骚动)的情况,并被它们所置换。同样地,这个现在分词在语法上的平静被一个隐藏的中音所干扰:草是擦热的,主动式,而考虑到唯一被擦热的就是它自身,它又是被动式的。这个分词也占据了及物和不及物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它的功能完全象一个草草做成的通行证,击溃读者并把他悬吊在不确定性的山谷之上的一个语义学手掌的魔法。读者已被第二行变成了一个将会在第十九行出现的“陌生人”。事实上,最开始的两个词把就读者放进了一个测验之中,因为我们并不能很快弄清楚“Who
stands…”引出的是一个问句还是一个名词性从句。这种句法趋向感的延置是一种完美的技术补偿,它弥补了诗中缺乏的对迫近的灾难的确定和直觉体察,它给这首诗一个无声的高潮和结尾。
虽然“擦热的”有这么多妙处,但它之被选取仍是无法解释的;它彻底免于那句未说出的“这是语言侦探的游戏”——这句话笼罩在更加谨慎、更加具有词典导向的晚年奥登身上,在他开始把他身上开阔、铿锵、流动的牛津词典变成线编拖鞋的时候。还记得《谢谢你,烟雾》一书的同题诗中拆散的羊毛:
不共戴天的敌人步态踉跄,
来自驾驶员和飞机的恐吓
当然,是会飞的,将降祸于你,
但我是如此地兴奋于
你已被诱引去造访
威尔特郡巫术般的乡间
在圣诞节的那一整个星期。
这“巫术般的”(witching)是漂亮的、纵容的,带着冷漠而迟滞的书面语感,虽然它自身灵巧的意味沾上了厌倦的气息,甚至对诗人本人而言也是如此(“步态踉跄”和“会飞的”亦是同样的情况)。尽管“擦热的”敲打着语言的岩石并从裂缝中带来突然的生命,这些后期所用的词语仍是收藏家的条目,在盛气凌人的快感之中启用,失去了加入到早期发现中的需要和愉悦。
高兴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再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了。后期奥登是诗歌的不同种类;到那时侯,诗句在它的个人小天地内部是教条主义者,想要象一根毛线一样抚慰人而不是象一截裸露的金属线一样令人震惊。伴随着整个操作过程的是在“让我们不再悲伤,最好去寻找/留在后面的东西里面的力量”一句中一种非自我怜悯的气氛,我引用的这一段只是想再次提醒你们四十年之后奥登诗歌在语言学姿态上的变化幅度。在最开始,盎格鲁—撒克森韵律的重压和盎格鲁—撒克森措辞的金属般的格言声响象一把耙子一样被人在社会言语和抑扬格抒情诗的天然斜坡上拖来拖去。诗歌没有顺水启程,它在混乱中争辩、摩擦、“在窗格上、在榆树皮上伤害自己”。在这罕见的音乐的旋涡之中所发生的正是艾略特所说的“集中”(concentration),一个他在讨论真实地被诗人经验过的情感和在诗中被表现——或者说得更好些,被发明——出来的情感之间的一度迫切的关系问题时所使用的术语。“我们不得不相信‘情感在宁静中被追忆起来’(译注:出自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是一个不正确的公式”,艾略特在《传统和个人才能》中这样写道,他又说:
因为它(诗歌)既不是情感,也不是回忆,更不是宁静,如果不把宁静曲解的话。它是一种集中,以及由这种集中产生出来的新东西,包含了极为可观的经验;诗歌的集中并不是有意识地或审慎地进行的。这些经验不是“被追忆起来的”,它们最终在一种气氛中融为一体,这种气氛只有在它被动地伴随着整个过程的情况下才是“宁静的”。
当我们阅读诸如《比白天更高》这类诗的时候,我们就置于这种“集中”之中。这首抒情诗既未跟随我们常识中的言语步伐,也不想模拟“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说话”的情感和语言常规;它更象是为我们展示那种“新的东西”,我曾暗示过,这种东西居住在生活经验附近或者与它平行,虽然它对那些活生生的经验饱含同情,但它不原定居在它们之中:
黎明时分的嘈杂将会把自由
带给某种寂静,但不是这种
没有鸟儿能反驳:短暂的——但足够用来
在这时辰里做某些事情——被爱的或者承受的。
它的宁静更多地和追忆时词语所完成的东西有关。或许,不是超越理解的寂静,而是抵抗解释的寂静;总之,一种“没有鸟儿能反驳”的寂静。
但如此一来,一只鸟儿的运动不是等于如此深的安静和满足之中的一种干扰甚至“反驳”吗?虽然诗中的鸟儿不知何故几乎不具备充分的肉体实在以使它能够反驳什么东西。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拿它和哈代的薄暮中的鹰比较,“穿过阴影落在/被风吹弯了的高山荆棘上”,我们知道哈代的鹰是一个拍击翅膀的可触的黑暗瞬间,是空中楼阁的滑落,是暮色中一个“从那儿出来”的现象,而奥登的鸟儿是一个“在这儿”的事件,是对能量的点燃,它发生在当某些活跃的、细瘦的、滴答作响的元音在敏捷的反应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鸟儿能反驳:短暂的——但足够用来/在这时辰里做某些事情——被爱的或者承受的。”这些诗行中对位法的、延宕的、被阻断的看与被看运动和它们被华丽制作出来的并未复杂化的意义一样重要。现代英语韵律的铁锤——就是被罗伯特·格雷称为叮当叮当的铁匠活的东西——正在古英语之桨更深层、更长远的摇动之中继续敲打,而耳朵——不管它对它所听到的东西的来源是如何漠然——注意到了这场角逐。这场角逐,完美地竞争着,虽有起伏但基本平衡,是在单一的、有方向的智力的航海成果和对它所操作的元素(语言自身的元素)的击打和投掷之间。
奥登的作品,从开始到最后,闪烁着活跃的智慧——在约瑟夫·布罗茨基看来,那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智慧。事实上,布罗茨基收在他最近的散文集《少于一》里面的关于奥登的文章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证据,它证明了当“死者的词语在生者的肺腑之中被修改”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一个诗人最终变成了他的景慕者。再没有比布罗茨基对《年9月1日》逐行逐句的评论更伟大的对诗歌的称颂了——它把诗歌作为全部人类知识的呼吸和精魂,我怀疑把如此欢跃、如此诚挚、如此权威的书写行为称为评论是否合适。他给奥登以决定性的信任,信任他把所有传统诗歌手段据为己有的辉煌征服,信任他对诗韵、格律、词汇和被暗示出来的他的文明而极度谦卑的心智的调和。虽然我们会承认布罗茨基对奥登的赞誉的公正性,我们仍会对狡黠作为一种元素在奥登诗歌中的消失感到遗憾:一种由雷勒夫的颤抖、由语言最初的“主要的悲哀,世界性的悲痛”形成的踪迹。艺术的价值——那种忠心地嫁给了祛魅和解毒的艺术、那种在涟漪的表面寻找纹理的形状的艺术、那种被推动去发号施令和维护公民的语言的艺术——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对语言自治的确切的限制,是对它的更野蛮的射击的刻意驯服。
仍然用马丁·布伯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奥登诗歌获得的对“它”的世界的统治越多,它所赋予亲密的“你”的世界的东西就越少。这些晦涩的早期诗歌是使人感到不便的,不自觉地说着原初的和彻底劝说性的语言。从措辞的文学感觉和口语感觉两方面来说,这些诗歌都是“激进的”——即使在它们谨守格律规则或者采用儿童故事书中的最初语言的时候:
因无叶之木而受饿
巨人们奔跑着咒骂他们的食物,
枭和夜莺哑然无声
天使将不会降临。
前面,不可能的严寒
举起了山峦可爱的头颅
它的白色瀑布庇护了
旅行者最后的忧伤。
虽然这首诗并没有在节奏的角度上回击调整好了的耳朵的期待,它的形而上地理学依然而后我们熟悉的“真实世界”中可安慰的等高线有所差别。比战后欧洲寓言诗歌早很长时间,奥登就抵达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被对厌恶之物的预兆所打击,并通过严格的诗歌手段充分地给予了那些预兆以表达方式。但是当奥登不可避免地驱使自己拓展自己,去超越传播由直觉获取的知识、超越诗歌的间接性和暗示性、开始以一种更加明晰、更有分析性和道德认可的修辞学书写那些直觉的时候,这种一体化的感知分裂了。在写一首象“西班牙”这样的诗的时候,不管它对场景的浓缩是多么惊险,不管它的意义是多么端庄,或者在写一首象“夏夜”这样的诗的时候,不管它的类似于基督之爱的用词是多么的莫扎特化,奥登已和他的孤独和怪异绝交。他指向人类大家庭的责任感变得剧烈、强大并且广受称颂,那些极度健康、富于沉思和判断性的、、年代的诗歌是其结果。我们或许会说这种意外的收获——它包括象《写给拜伦王的信》这样的早期杰作和象《石灰石颂歌》这样的晚期作品——代表了对在《俄尔甫斯》一诗中提出问题的回答。这个回答倾向于说:“歌”最希望得到“生活的知识”,倾向于逃避所提供的选择——“去迷惑或者去快乐”
——中“迷惑”的系数。作为另外一种应对办法,奥登最后认定生活集中在“丰饶”之物中而不是“奇异”之物,如果我们认为诗歌的持续推动力完全是普罗斯彼罗式的,它被引向把人类安置到宇宙性安全之中的理性方案里面,这种选择就是可理解的。然而作为早期在30年代的“奇异”诗歌的特征的厄运和预兆、它的迷惑和悬而未决的视像,仍然把英语诗歌带到了离可怕的想象力的边界一度是最近的地方,并提供了一个例证:二十世纪人类是怎样承受的孤立的经验和普遍的震惊的从此可以从英语之中测听到。此外,在他晚年的诗歌中,当类似的音符敲响的时候,诗歌不可避免地增强了可铭记性和强度:
没有财富或者怜悯,
红腿的小鸟,
坐在它们的花斑蛋上,
看着染上流感的城市。
与此同时,在别处,
大群驯鹿穿过
一片又一片金色的苔藓地,
安静而迅速。
奥登的魅惑作者:詹姆斯#;芬顿翻译:王敖一
在牛津读本科的时候,
奥登纵观当时的文坛并认定它提供着一个空的舞台。“显然他们在期待某个人的出现”,他对斯蒂芬#;史本德(Stephen
Spender)说,而后者告诉我们,“他很快就会占据那种期待气氛的中心位置。”无论如何,奥登的梦想是去做中心而不是唯一的人物。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将成为小说家,罗伯特#;迈德雷RobertMedley)将成为画家,西塞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刘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和史本德则以诗见长。史本德曾对奥登说他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去写散文,但奥登明确反对,“你应该只写诗歌而不写其它的东西,我们不希望在诗歌上失去你。”“可你真觉得我是那块材料吗?”
史本德露怯地问,“当然”,奥登冷峻地回答他。“可为什么?”“因为你是那么有能力去被羞辱。艺术是从羞耻中诞生的。”
史本德后来还是写了些散文,包括上面引用的他的自传《世界中的世界》(WorldWithin
World),还有我强力推荐的他的一本不常见的书《欧洲见证》(European
Witness)。他的日记很重要,而且他也和戴#;刘易斯一样写小说。真正的固守疆界的行为是发生在杰出的诗人奥登和杰出的小说家依修伍德之间。依修伍德远离诗歌,除了一些早期的韵文和若干翻译。奥登则力避一切象小说的东西。他们两人合作过戏剧—那是一个他们可以友善地分割的领域。依修伍德编电影剧本,而奥登为纪录片写作出色的文案,其中的两个(《采煤现场》(Coal
Face)和《夜邮》(NightMaid)
)本身就是诗。依修伍德后来参与了一步关于弗兰根斯坦的电影,稍后乔纳森#;济慈提议给它加一个副标题“莫里斯先生换大脑”(Mr.
NorrisChangesBrains)。奥登去做歌剧,依修伍德则进军好莱坞,两人都不去碰对方的地盘。
然而,散文不可能被单独划分出来或者被抛开,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对史本德是如此,对奥登也一样。散文是个过于重要的,过于难以令人满意的概念,而且散文在它的各种分支之中显得过于有趣了。怎么可能把诗歌交给奥登,把小说交给依修伍德,而把散文交给史本德?这是不可相加也不可划分的。而且,奥登也需要散文。
他以不同的方式需要散文,其中之一是为了生计。正如他在《染匠之手》(TheDyer”s
Hand)一书的介绍中所说,他写作他所有的讲座发言稿,介绍和评论都是因为他需要稿酬。他希望一些爱能够贯穿在这些写作中。但当他再次审视自己的批评文章的时候,他决定把它们缩减成一系列笔记。阿兰#;安森(Alan
Ansen)编辑过一个奥登的“闲谈”的集子,年的时候他曾经对奥登说,“我觉得你也许将要出版一卷散文汇编”,奥登说,“我不这么认为。批评应该是不经意的对话。”
他的“闲谈”和《染匠之手》开头的段落确实非常相似:
一个诗人最痛苦的经验是发现他的一首他知道是假冒品的诗已经满足了公众而且进入了选本。尽管他知道这诗可能是不错的,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本不该写它。
没有哪个诗人或者小说家希望他是曾经存在过的唯一的一个,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希望自己是活着的唯一的一个,而且很多人愉快地相信他们这一希望已经成真。
一些书被冤枉地忘记了;没有哪本书被冤枉地记住了。
一个人无法在评论一本坏书的时候不去卖弄。
这些都是来自书上,而下面这个来自谈话:
叶芝用他前半生的时间写次要的诗歌,用后半生的时间写如何做次要诗人的重要的诗歌。
再看这个:
无论如何,除了《小老头》(Gerontion)以后的诗歌(微笑),艾略特什么都没写。
安森加入“微笑”一词来表示奥登意识到他所说的并不是真的。
奥登给期刊写的批评文章很长时间都不整理,到后来他自己都忘了他写过的很多东西还有在哪里能找到它们。《染匠之手》首次出版于年,由一位助手在奥登的指导下收集而成,他的工作就是去图书馆复制被疑似的篇什。大概奥登由此开始准备配套的随笔。十年后出版的《序跋选》(Forewords
andAfterwords,)首次收集了奥登三十年代写的报刊文章,此书由爱德华#;孟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选编并审查,他是奥登文学作品的委托管理人和《英国奥登》(English
Auden,)的编者。此书出版之际,只有很少数的拥有长期记忆的细心的读者才会对奥登的全部作品有所理解。我还要提一下,孟德尔森近期出版的权威性的合集—《散文--》(Prose
-)仅仅是收集奥登的佚文的开始。尽管我们现在比不久前有更好的位置去观照整体的奥登,我们只有看到他的全部散文之后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个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期待着他的散文胜过他的诗,或者用散文去补足他的诗中已经被觉察到的缺陷,而在于奥登著作中的散文和诗在互相贯通和渗透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任何其它本世纪的英语诗人。 在奥登的著作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布莱克的影响和后期的亨利#;詹姆斯的影响,二者同样在诗和散文中留有踪迹:剑在贫瘠的石楠上歌唱
镰刀在富饶的田地之中:
剑唱他的死亡之歌,
但不能让镰刀屈服。
阿米巴虫在流水中
生命在儿女中更新
“山谷上悬的利剑”
虫子对钢蹦儿说道
红的肢体,火焰般的头发上,
禁戒洒满了沙;
但是满足的欲求,
种起生命的与美的果实。
不愿思考者
毁于这行动:
不愿行动者
毁于这理智
无矛盾则无进步。吸引和推斥,理智和能量,爱和恨,是人类存在之必需。
承担一切的人认为他如此行事是出于责任感,他是在自欺而且将毁掉一切他所触及的东西。
抑制欲望的人如此作为是因为他们的欲望虚弱到能被抑制的程度;而抑制者或者理智篡夺它的领地并且统治非自愿的东西。
丰富者和饕餮者:艺术家和政客。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敌人,也就是说,他们每个都有一个对方无法理解的世界,进而言之,政客和艺术家也有好有坏
,这些好的人必须学会去尊重对方。
饕餮者觉得似乎生产者被缚在他的锁链之中;但并非如此,他仅仅是得到了存在的一部分就幻想得到了全部。
但丰富者将不再丰富,除非饕餮者,象海一样,取得他过剩的快乐……
这两种人永存在大地上,而且他们应该是敌人:任何试图调和他们的人都要损毁存在。
以上散文的顺序是:布莱克,奥登,布莱克,奥登,布莱克,奥登,布莱克。我去掉了布莱克用的。
赞赏
人赞赏
海口白癜风专科医院白癜风医院合肥哪家好转载请注明:http://www.gdnyy.com/wazz/821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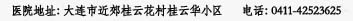
当前时间:
